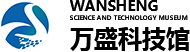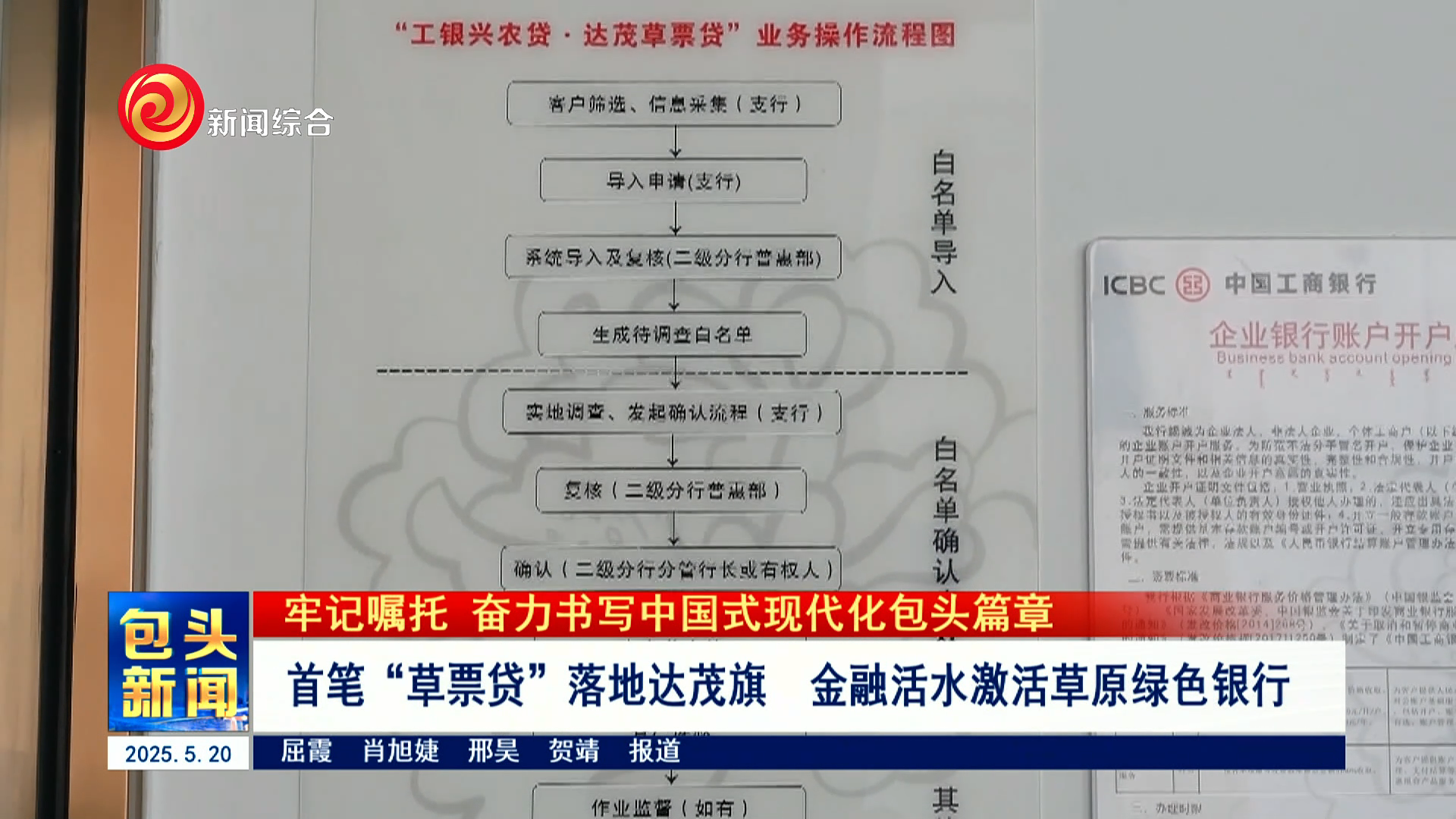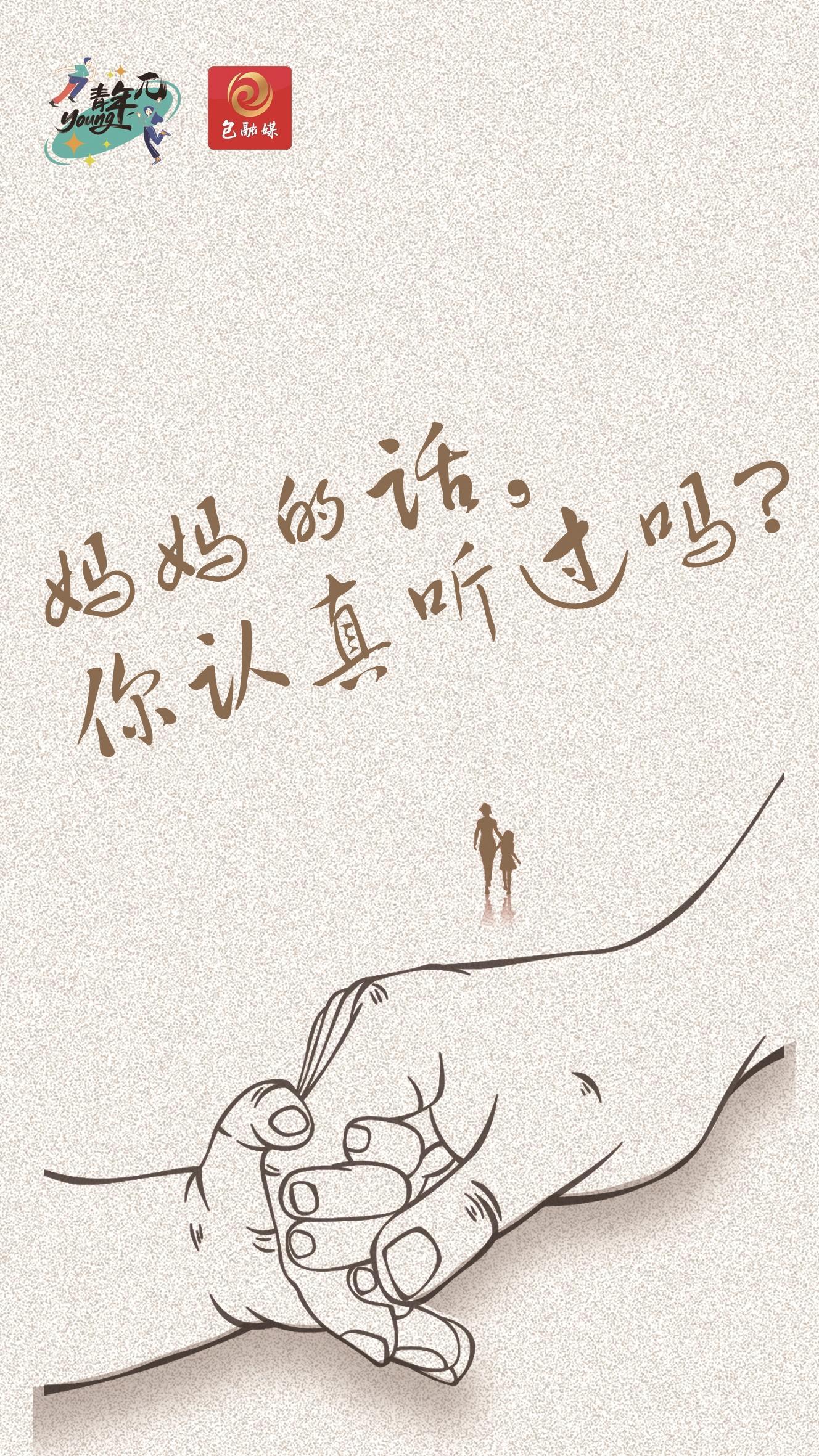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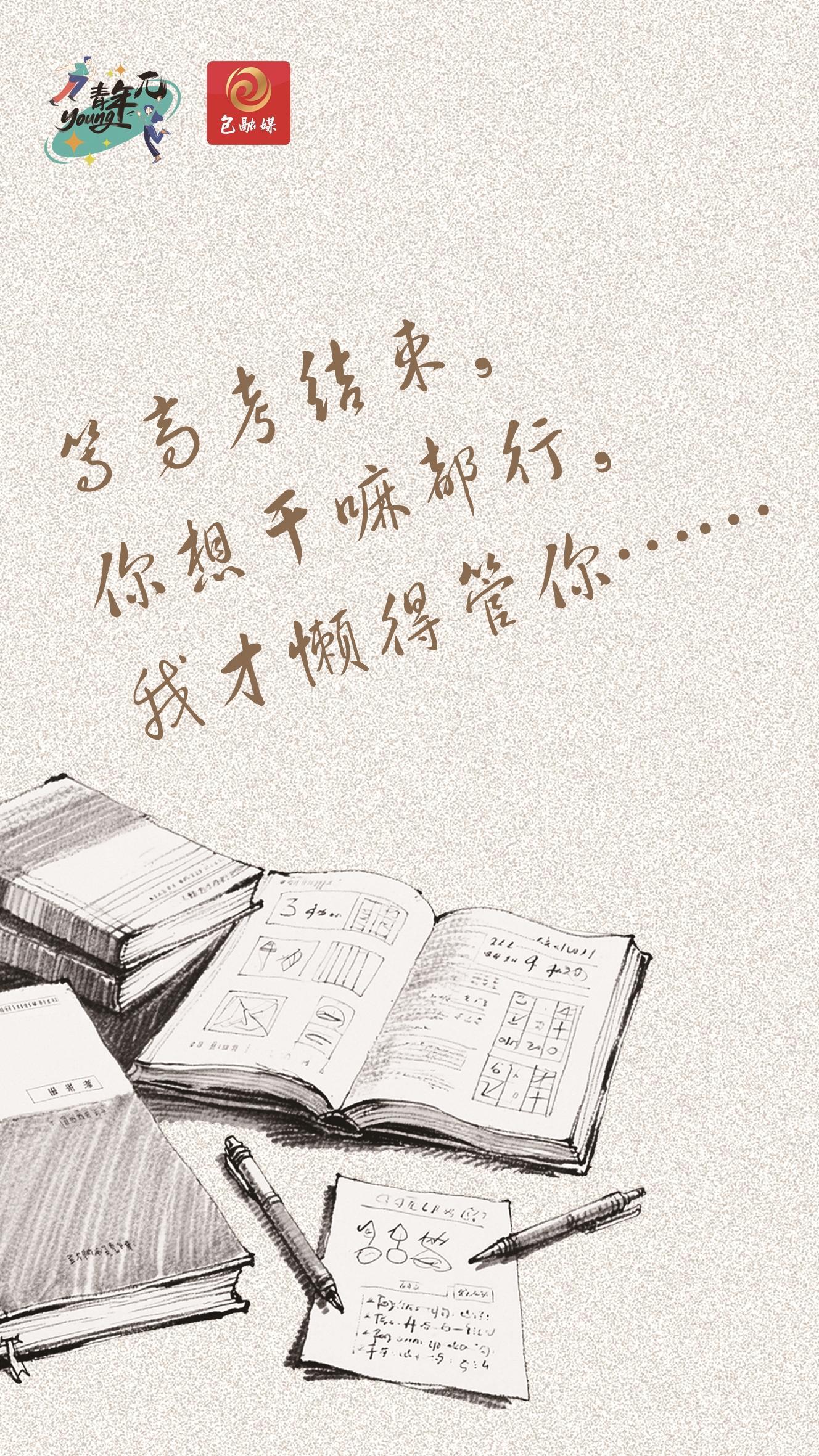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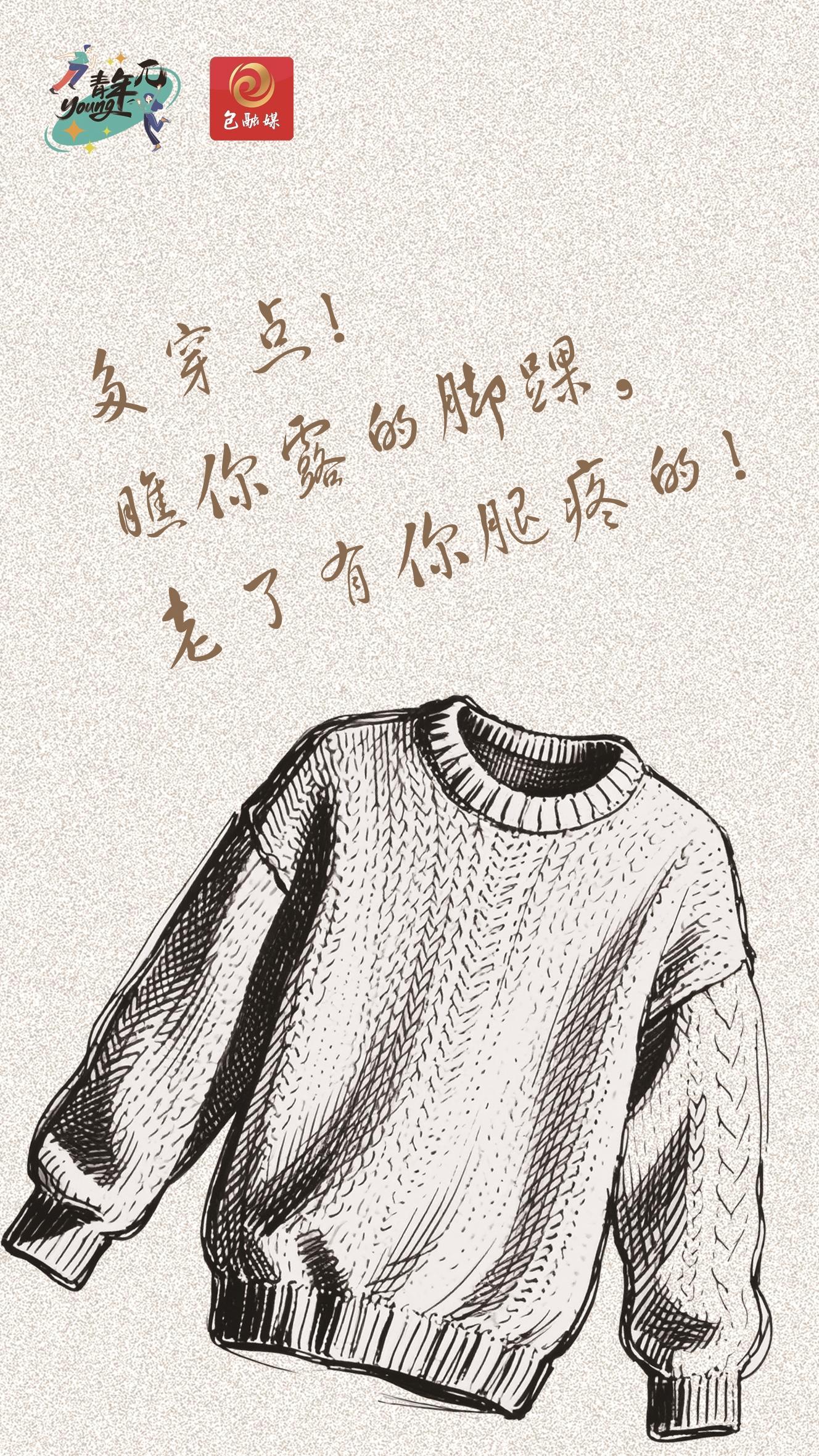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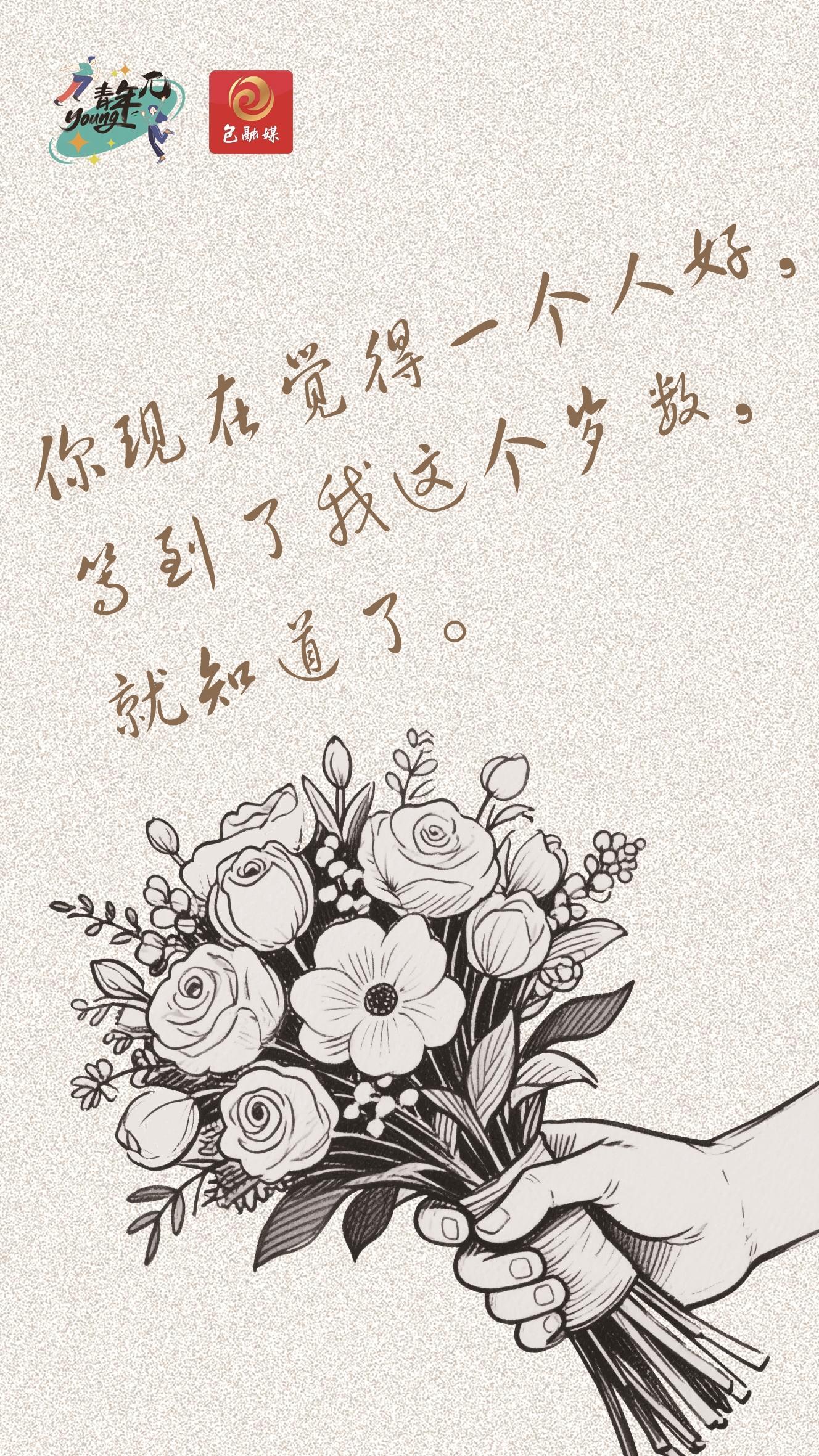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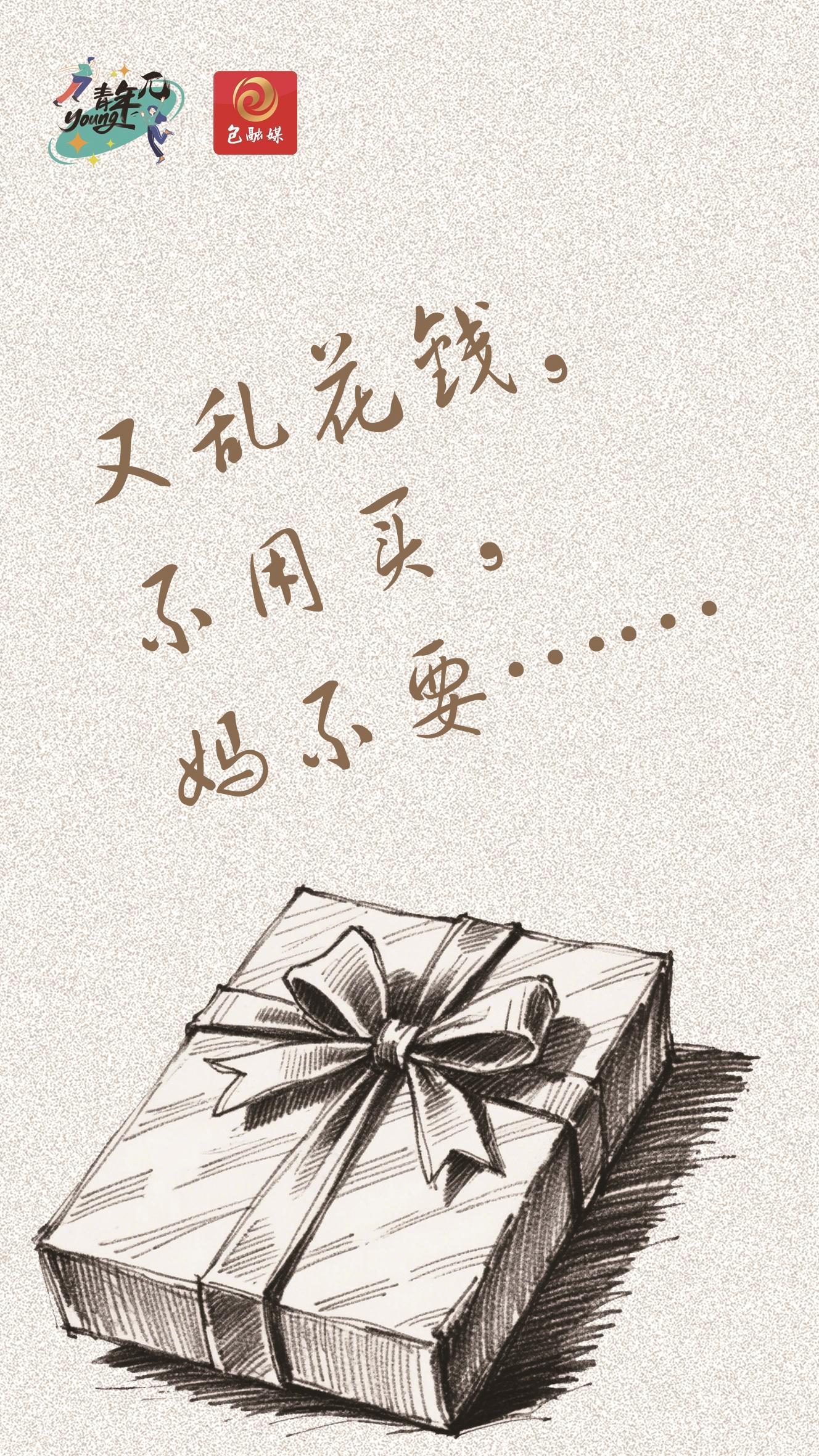
□策劃/賀怡欣 鄧雅鑫
記者/鄧雅鑫 李春燕 曹瑾
海報(bào)制作/高軒 制圖/張春霞
在時(shí)光的長(zhǎng)河中,母愛(ài)如蜿蜒的河流,以不同的姿態(tài)滋養(yǎng)生命的原野。這個(gè)母親節(jié),我們走近五位母親——“國(guó)家的孩子”李焱飆,講述大愛(ài)無(wú)疆的傳奇;福利院“媽媽”侯夢(mèng)婕,以點(diǎn)滴溫暖縫合命運(yùn)的裂痕;將三個(gè)孩子送往名校的莊冬梅,詮釋“教育是彼此照亮”的智慧;初為人母的幼師,在瑣碎中擁抱遲來(lái)的圓滿;還有無(wú)數(shù)平凡母親,用煙火日常編織溫柔的鎧甲。她們的故事或宏大或細(xì)微,卻同樣鐫刻著時(shí)代的印記。我們以傾聽(tīng)為舟,溯流而上,在母愛(ài)的敘說(shuō)中,觸摸那些歲月里的深情。



我是“國(guó)家的孩子”李焱飆,在這個(gè)母親節(jié),我將隨女兒遷往新的城市。站在人生第六十個(gè)年頭回望,我家三代女性的命運(yùn)軌跡,恰似一條蜿蜒的河流,與祖國(guó)母親的脈搏同頻共振,交織成一部鮮活的時(shí)代發(fā)展史。
我的養(yǎng)母生于解放前,作為家中獨(dú)女,8歲便被送去當(dāng)童養(yǎng)媳。直到新中國(guó)成立,她才從舊社會(huì)的枷鎖中掙脫,重獲“女兒”的身份。盡管以優(yōu)異成績(jī)完成小學(xué)學(xué)業(yè),卻因家境貧寒,只能放棄升學(xué),進(jìn)入速成師范。這段求學(xué)的遺憾,反而化作她育人的執(zhí)著。在三尺講臺(tái)上,她培養(yǎng)出龍梅、玉榮等優(yōu)秀學(xué)生,更將無(wú)私的母愛(ài)給了我——一個(gè)來(lái)自上海的孤兒。
1963年,我出生在遭受自然災(zāi)害的上海,成為眾多棄嬰之一。是黨和政府的關(guān)懷,讓我從上海市兒童福利院踏上北行列車,跨越千里來(lái)到內(nèi)蒙古草原。在這里,我被草原額吉收養(yǎng),既感受著養(yǎng)母的溫情,也沐浴著祖國(guó)母親的庇護(hù)。從孤兒到大學(xué)生,從受助者到講述者,如今退休的我,總愛(ài)在公益課堂上分享“三千孤兒入內(nèi)蒙”的故事,那段跨越血緣與地域的大愛(ài)傳奇。
我的女兒1990年出生于達(dá)茂旗,從草原小鎮(zhèn)到上海名校,再到如今理想的工作崗位,她的每一步跨越,都印證著新時(shí)代青年的無(wú)限可能。
我常想,我們家三代女性的故事,何嘗不是中國(guó)發(fā)展的微觀注腳?養(yǎng)母掙脫舊社會(huì)的桎梏,在新中國(guó)重獲新生;我在國(guó)家的羽翼下走出困境,成長(zhǎng)為時(shí)代的見(jiàn)證者;女兒則在繁榮開(kāi)放的時(shí)代浪潮中實(shí)現(xiàn)理想。這一路,從上海保育院的醫(yī)生阿姨,到遷徙途中的保育員額吉,再到無(wú)數(shù)給予我溫暖的“母親”,是她們共同托舉起我的人生。而最堅(jiān)實(shí)的依靠,始終是祖國(guó)母親。值此母親節(jié),我想對(duì)所有母親道一聲感謝,因?yàn)槟膹?qiáng)大,才讓千萬(wàn)個(gè)“我”的故事,都成為希望與愛(ài)的傳奇。

我是莊冬梅,內(nèi)蒙古園丁教育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創(chuàng)始人,也是三個(gè)孩子的母親。目前大女兒正在北大攻讀博士學(xué)位,大兒子從倫敦政治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碩士畢業(yè),小兒子在日本留學(xué)。
常有朋友問(wèn)我如何平衡事業(yè)與家庭,我的答案始終是——教育不是單方面的付出,而是全家共同成長(zhǎng)的過(guò)程。因?yàn)閯?chuàng)業(yè),我沒(méi)有大把的時(shí)間陪伴在孩子身邊,所以我的孩子是野蠻生長(zhǎng)的。很多人以為“放手教育”就是撒手不管,其實(shí)恰恰相反,我對(duì)孩子們的影響和教育從未缺席。我的孩子們都知道,在家里,學(xué)生做好學(xué)業(yè),我經(jīng)營(yíng)好書店,丈夫教好書,每個(gè)人必須守住自己的“責(zé)任田”。同時(shí)這些年我悟出,真正的陪伴未必需要大塊時(shí)間,和孩子組隊(duì)打游戲,窩在沙發(fā)共讀一本書,甚至只是認(rèn)真聽(tīng)他們講新學(xué)的網(wǎng)絡(luò)用語(yǔ),都是心靈靠近的契機(jī)。這樣良好的家庭氛圍給我們帶來(lái)了意想不到的收獲。
還記得在我雙胞胎兒子小學(xué)時(shí)的一個(gè)婦女節(jié),我在書店接待朋友,兩個(gè)孩子突然跑來(lái)要100元,那會(huì)兒這筆錢不算小數(shù)目,我礙于面子給了錢,又忐忑不安,生怕他們亂花。深夜回家推開(kāi)門的瞬間,眼淚直接砸了下來(lái)——兩個(gè)小人兒餓著肚子守在蛋糕前睡著了,蛋糕上寫著“媽媽節(jié)日快樂(lè)”,直到現(xiàn)在每逢節(jié)日,我辦公室總會(huì)出現(xiàn)帶著露珠的鮮花。
我的女兒從小就獨(dú)立,但高中有段時(shí)間,原本年級(jí)前十的成績(jī)突然滑到百名開(kāi)外,老師經(jīng)常打電話,孩子整日也焦慮。我硬是忍著沒(méi)嘮叨,帶她見(jiàn)了多位優(yōu)秀的朋友,帶她去了解更廣闊的世界。直到有天她主動(dòng)說(shuō):“媽媽,給我請(qǐng)個(gè)補(bǔ)習(xí)老師吧。”那瞬間我知道,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覺(jué)醒比任何催促都有力。
現(xiàn)在看著三個(gè)孩子在不同時(shí)區(qū)為理想奮斗,書房里還留著他們從小到大的讀書筆記。每當(dāng)有人夸我把孩子培養(yǎng)得多優(yōu)秀,我總想起那個(gè)婦女節(jié)的蛋糕——教育從來(lái)不是單行道,我們始終在彼此照亮。

清晨,我照例沿著兒童部的走廊走了一圈,陽(yáng)光斜斜地爬上教室的窗沿,幾個(gè)小腦袋從門框邊探出頭來(lái)。我是侯夢(mèng)婕,今年是我在福利院工作的第十三個(gè)年頭,看著這些可愛(ài)的孩子,總會(huì)想起當(dāng)年那個(gè)手足無(wú)措的自己。
2012年剛到這里時(shí),我才23歲。第一次見(jiàn)到這么多殘疾兒童,尤其有些孩子明明不是重病,卻被親生父母拋棄,那種不理解的情緒堵在胸口,有說(shuō)不出的心酸。最開(kāi)始我完全不知道該怎么幫助他們,總覺(jué)得自己的力量太過(guò)于渺小,直到發(fā)現(xiàn)這些孩子的純粹,你只要付出一點(diǎn)愛(ài),他們就會(huì)用百分百的真誠(chéng)回應(yīng)你。
還記得有個(gè)不會(huì)走路、不會(huì)說(shuō)話的孩子,觸覺(jué)遲鈍到走路都能睡著。我?guī)е隹祻?fù)訓(xùn)練,每天重復(fù)教最簡(jiǎn)單的動(dòng)作,用了兩三年時(shí)間,終于看到他搖搖晃晃邁出第一步,開(kāi)始說(shuō)話,反應(yīng)也變得靈敏了。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,也讓我明白了這份工作的意義。
這份工作讓我感受到沉甸甸的責(zé)任與意義——雖非親骨肉,依然父母心。后來(lái),我結(jié)婚有了自己的孩子,便更加能體會(huì)到母親的心情。看到孩子搶救時(shí)心急如焚,見(jiàn)他們悶悶不樂(lè)就陪著聊天開(kāi)導(dǎo),他們想要玩具或別的東西,我也會(huì)盡量滿足——這170多個(gè)可愛(ài)的孩子,既然命運(yùn)沒(méi)給他們父母的愛(ài),我這里總要漏點(diǎn)光。
目前我負(fù)責(zé)兒童養(yǎng)育的整體管理工作,最欣慰是看到孩子們吃飯香了,游戲時(shí)笑聲多了,護(hù)理員們工作有勁頭了。窗臺(tái)上小家伙偷偷放野花,過(guò)節(jié)時(shí)辦公桌上歪歪扭扭的賀卡,這些瞬間讓我覺(jué)得,當(dāng)初那個(gè)心痛的姑娘,早被這些小手捂暖了。

周末清晨,我倚著飄窗看父子倆在小區(qū)晨跑。十三歲少年奔跑時(shí)飛揚(yáng)的校服衣角,像一面流動(dòng)的旗幟,瞬間將我拽回往昔——那個(gè)曾攥著我食指蹣跚學(xué)步的奶娃娃,何時(shí)已長(zhǎng)成挺拔的少年?案頭青瓷瓶里斜插著新開(kāi)的百合,潔白花瓣舒展,恰似我們一家三口平淡又溫暖的日常剪影。
深夜,兒子書桌上的臺(tái)燈總是亮著。有時(shí)端著溫?zé)岬呐D掏崎T進(jìn)去,臺(tái)歷本里夾著的詩(shī)句便映入眼簾——那是我抄贈(zèng)的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墨跡暈染在月考倒計(jì)時(shí)旁。少年伏案的脊背繃成一道倔強(qiáng)的弧線,像棵在夜色里拔節(jié)的竹,把成長(zhǎng)的酸澀與疼痛都化作筆尖沙沙的聲響。牛奶杯壁凝著細(xì)密水珠,在暖黃燈光下折射出細(xì)碎的光,恍惚間,我仿佛又看見(jiàn)幼兒園入園那日,你攥著奧特曼玩偶,蹦跳著替哭泣的小朋友擦去眼淚的模樣。
上個(gè)月整理書柜時(shí),我發(fā)現(xiàn)那摞翻卷邊的《貓武士》上,壓著嶄新的《了不起的敦煌》。曾經(jīng)舉著紙望遠(yuǎn)鏡,信誓旦旦說(shuō)要探索宇宙的小男孩,如今已將航天模型擺滿整個(gè)書柜。當(dāng)你與父親熱烈討論航天知識(shí)時(shí),眼睛里閃爍的光芒,讓我讀懂了你作文里那句“愿乘蒼茫云海,不辭冰雪長(zhǎng)路”的熾熱。少年啊,愿你永遠(yuǎn)保有擦拭他人眼淚時(shí)的溫柔,也永遠(yuǎn)懷揣刺破蒼穹的銳氣,讓七歲時(shí)疊的紙船,終有一日化作劈波斬浪的巨帆,載著赤子之心駛向星辰大海。
晨光里,百合又綻放兩朵,清甜的香氣漫過(guò)你留在餐桌上的便簽:“媽,記得喝牛奶”。端起杯子,溫?zé)岬挠|感從掌心傳來(lái),記憶突然閃回產(chǎn)房——第一次將皺巴巴的你貼在胸口時(shí),那種血脈相連的震顫仿佛仍在。原來(lái)所謂養(yǎng)育,不過(guò)是看著那個(gè)渾身奶香的小肉團(tuán),漸漸長(zhǎng)成會(huì)牽著我過(guò)馬路的翩翩少年。而歲月最珍貴的饋贈(zèng),正是你奔跑時(shí)飛揚(yáng)的衣襟,那永遠(yuǎn)差半步就能觸及的距離,讓我既欣慰又不舍地見(jiàn)證著,你走向?qū)儆谧约旱倪h(yuǎn)方。

2024年10月的一天,33歲生日那天的我,被送入產(chǎn)后觀察室,終于等來(lái)了這場(chǎng)遲到卻珍貴的相遇。懷中那個(gè)皺巴巴的小生命正攥著我的手指,像是攥緊了我余生所有的溫柔。
作為一名幼師,十余年的職業(yè)生涯里,我教會(huì)孩子們系鞋帶、唱兒歌,在他們跌倒時(shí)給予擁抱。那些在幼兒園哄睡哭鬧孩子的夜晚,那些編排親子活動(dòng)的周末,原來(lái)都是命運(yùn)安排的預(yù)習(xí)課。但當(dāng)我真正成為母親的那一刻才明白,所有過(guò)往的經(jīng)驗(yàn),都不及眼前這個(gè)小生命帶來(lái)的震撼。
與丈夫的相遇像是老天特意安排的驚喜。在經(jīng)歷過(guò)幾段無(wú)果的感情后,我們?cè)谂笥训木蹠?huì)上偶然相識(shí)。他理解我對(duì)事業(yè)的執(zhí)著,支持我繼續(xù)在幼教崗位上發(fā)光發(fā)熱;我欣賞他的沉穩(wěn)可靠,也珍惜他給予的安全感。我們共同經(jīng)營(yíng)著一個(gè)充滿歡笑的小家,直到這個(gè)小生命的降臨,讓幸福變得具象。
孕期的每一次胎動(dòng)都像命運(yùn)的暗示,提醒著我即將開(kāi)啟人生新的篇章。盡管高齡產(chǎn)婦的身份讓產(chǎn)檢變得格外謹(jǐn)慎,但丈夫始終陪伴在側(cè),細(xì)心記錄著每一個(gè)珍貴瞬間。當(dāng)醫(yī)生宣布母子平安的那一刻,我看著丈夫紅了眼眶的模樣,突然意識(shí)到,我們共同創(chuàng)造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奇跡。
如今,清晨第一縷陽(yáng)光爬上嬰兒床時(shí),寶寶粉撲撲的臉蛋會(huì)跟著泛起柔光。他無(wú)意識(shí)地咂咂嘴,睫毛在眼下投出扇形的影子,我常常就這樣托著下巴,忘記了時(shí)間。那些換尿布、拍嗝的瑣碎日常,在他第一次含糊不清地喊出“媽媽”時(shí),都成了甜蜜的勛章。這個(gè)小小的生命,讓我重新理解了“被需要”的意義,也讓我慶幸歲月讓我有足夠的閱歷與從容,去擁抱這份遲來(lái)的圓滿。原來(lái)人生最好的安排,永遠(yuǎn)會(huì)在最恰當(dāng)?shù)臅r(shí)刻到來(lái)。
■青年說(shuō)



□鄧雅鑫
母親的身份從無(wú)定式。有人以血脈為紐帶,在柴米油鹽中編織守護(hù);有人以責(zé)任為橋梁,為陌生的生命點(diǎn)亮歸途;有人以理想為風(fēng)帆,與孩子并肩探索世界的遼闊。從“國(guó)家的孩子”李焱飆跨越時(shí)代的感恩,到福利院“媽媽”侯夢(mèng)婕日復(fù)一日的守候;從莊冬梅與子女彼此照亮的成長(zhǎng),到新手母親在瑣碎中拾取的圓滿,再到無(wú)數(shù)平凡母親將歲月熬成溫?zé)岬臏齻兊墓适禄蛉缃颖加浚蛉缦黛o默,卻始終指向同一個(gè)內(nèi)核:愛(ài)是永恒的底色。
這份愛(ài)可以是草原額吉跨越千里的懷抱,是福利院窗臺(tái)上一束帶著露珠的野花,也是孩童小心翼翼守護(hù)的一塊蛋糕。它不囿于血緣,不拘于形式,卻能穿透時(shí)光的褶皺,沉淀出最堅(jiān)韌的力量。當(dāng)我們凝視這些母親的身影,傾聽(tīng)她們的訴說(shuō),看到的不僅是個(gè)人故事的起伏,更是千萬(wàn)種母愛(ài)所凝結(jié)成的共同言語(yǔ)。
(編輯:吳存德;校對(duì):霍曉霞;一讀:張飛、黃韻;一審:張燕青;二審:賈星慧;三審:王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