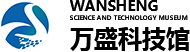名家對(duì)談
在文化同質(zhì)化日益凸顯的當(dāng)下,地域性寫(xiě)作如何以獨(dú)特的土地肌理構(gòu)建文學(xué)辨識(shí)度?其作為文化根脈與時(shí)代鏡像的雙重價(jià)值又該如何激活?5月25日,“包融閱時(shí)光”第四期讀書(shū)會(huì)——包訥睿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《橙灰的天際》分享會(huì)暨關(guān)于文學(xué)地域性的文學(xué)對(duì)話會(huì)在包頭市圖書(shū)館啟幕。
這場(chǎng)由文學(xué)界、評(píng)論界、出版界專(zhuān)家學(xué)者與本土文化名人共同參與的思想碰撞,以“地域性寫(xiě)作的重要性與獨(dú)特性”為核心議題,展開(kāi)了一場(chǎng)理論與實(shí)踐交融的思想碰撞,為本土文學(xué)與地域文化的當(dāng)代表達(dá)提供了多元解答。
時(shí)代經(jīng)緯的細(xì)密編織
包頭師范學(xué)院文學(xué)院教授、包頭市評(píng)論家協(xié)會(huì)副主席、青山區(qū)作協(xié)主席田中元以關(guān)于《橙灰的天際》所展示的文學(xué)時(shí)代視野為題,展開(kāi)了對(duì)這部作品的獨(dú)到見(jiàn)解。
田中元介紹,《橙灰的天際》以恢弘筆觸聚焦20世紀(jì)90年代的改革浪潮,通過(guò)三位青年十年間的奮斗史詩(shī),細(xì)膩勾勒出個(gè)人命運(yùn)與家國(guó)脈絡(luò)的深度交織。這部70萬(wàn)字的長(zhǎng)篇力作,以國(guó)企改革的壯闊進(jìn)程為經(jīng),以民營(yíng)經(jīng)濟(jì)的崛起脈絡(luò)為緯,更將港澳回歸的歷史時(shí)刻織入敘事肌理,在時(shí)代洪波中剖視人性的掙扎與覺(jué)醒。“宏大的架構(gòu)、鮮活的人物、跌宕的故事,讀來(lái)酣暢淋漓,令人沉浸于時(shí)代的風(fēng)云際會(huì)之中。”田中元的解讀,精準(zhǔn)提煉出作品兼具歷史縱深與人性溫度的創(chuàng)作特質(zhì)。
田中元在分享中,對(duì)作品展開(kāi)深度解讀。他認(rèn)為,《橙灰的天際》將時(shí)代精神與地域特色熔鑄一體,構(gòu)建出極具感染力的文學(xué)圖景。作家以親歷者的視角,將時(shí)代背景化作創(chuàng)作底色,憑借真實(shí)鮮活的取材,成功營(yíng)造出強(qiáng)烈的代入感與時(shí)代氣息。作品扎根生活土壤,以飽滿(mǎn)的故事、立體的人物塑造,展現(xiàn)出深厚的生活底蘊(yùn)與鄉(xiāng)土情懷。作家巧妙地將家國(guó)敘事交織融合,以微觀個(gè)體命運(yùn)映射宏觀時(shí)代變遷,通過(guò)“以小寫(xiě)大、以點(diǎn)帶面”的敘事策略,賦予作品厚重的歷史縱深感與思想張力。更值得稱(chēng)道的是,作品將民族精神與時(shí)代情緒有機(jī)滲透于字里行間,不僅深化了主題內(nèi)涵,更拓展了文學(xué)表達(dá)的思想維度。田中元以深厚的學(xué)術(shù)功底和敏銳的文學(xué)觀察力,為讀者們揭示了這部作品獨(dú)到的魅力。
包訥睿分享創(chuàng)作歷程
書(shū)寫(xiě)道路的“三重進(jìn)階”
讀書(shū)會(huì)現(xiàn)場(chǎng),包訥睿娓娓道來(lái)自己的創(chuàng)作歷程。他憶起童年時(shí)光,自小生活在農(nóng)村,當(dāng)?shù)厥⑿械亩伺_(tái)小戲成為他藝術(shù)啟蒙的源頭——每至傍晚,父母總會(huì)帶著他與哥哥姐姐一同聽(tīng)?wèi)颍切┮謸P(yáng)頓挫的唱腔與鮮活的舞臺(tái)形象,為他推開(kāi)了最早的藝術(shù)之門(mén)。上學(xué)后,同學(xué)家的小人書(shū)成為他接觸圖文閱讀的起點(diǎn),搭配收音機(jī)里傳統(tǒng)文學(xué)的生動(dòng)演繹,一顆關(guān)于寫(xiě)作的種子在少年心中悄悄埋下。
“興趣是創(chuàng)作的第一動(dòng)能。”包訥睿感慨道。進(jìn)入大學(xué)后,他迎來(lái)了創(chuàng)作積累的第二階段。一門(mén)《巴爾扎克專(zhuān)題研討》課程,如同一把鑰匙,為他打開(kāi)了外國(guó)文學(xué)的廣袤天地。他一頭扎進(jìn)托爾斯泰、雨果、福克納等大師的文字世界,在經(jīng)典作品中尋覓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范式,這些跨越時(shí)空的精神對(duì)話,讓他在文學(xué)探索中少了幾分迷茫,多了些方向感。
工作后分配至偏遠(yuǎn)鄉(xiāng)村的經(jīng)歷,成為他創(chuàng)作之路的關(guān)鍵轉(zhuǎn)折。圖書(shū)室里的《紀(jì)伯倫文集》與《泰戈?duì)栐?shī)集》,以詩(shī)性的哲思與浪漫的筆觸,引領(lǐng)他踏上真正的創(chuàng)作實(shí)踐——詩(shī)歌成為他文學(xué)初試的園地,那些凝練的文字里,藏著他對(duì)生活的觀察與思考。懷揣對(duì)文學(xué)的更深向往,若干年后,包訥睿考入中國(guó)傳媒大學(xué),《橙灰的天際》的創(chuàng)作藍(lán)圖正是在此時(shí)開(kāi)始勾勒。從童年的藝術(shù)啟蒙,到求學(xué)階段的經(jīng)典浸潤(rùn),再到工作后的詩(shī)歌試水,他將興趣的火種、對(duì)大師技法的研習(xí)、對(duì)生活的細(xì)膩體悟熔鑄一爐。“任何創(chuàng)作都始于興趣,歷經(jīng)模仿、實(shí)踐與淬煉,最終在歲月沉淀中找到屬于自己的表達(dá)。”包訥睿的講述,既是一部個(gè)人創(chuàng)作的成長(zhǎng)史,亦是一位寫(xiě)作者與時(shí)代、土地、經(jīng)典對(duì)話的精神獨(dú)白。
扎根土地探尋文學(xué)根脈
地域性寫(xiě)作如何突破邊界,在時(shí)代圖景中留下獨(dú)特印記?在包頭文學(xué)的脈絡(luò)里,從“文學(xué)旗幟”許淇以大青山叩開(kāi)全國(guó)視野,到當(dāng)代作家以“鋼藍(lán)色”工業(yè)記憶、地方產(chǎn)業(yè)故事呼應(yīng)時(shí)代心跳,一條清晰的創(chuàng)作路徑正在浮現(xiàn)——那便是以土地為根脈,讓地域文化成為文學(xué)穿越時(shí)空的靈魂密碼。
中國(guó)作協(xié)會(huì)員、資深作家車(chē)夫,本土文化名人、著名藏書(shū)家馮傳友等創(chuàng)作者的實(shí)踐與思考,正印證著“越本土越世界”的創(chuàng)作真理,也為地域性寫(xiě)作提供了極具啟示性的樣本。
談及地域性寫(xiě)作的標(biāo)桿,車(chē)夫多次提及“包頭文學(xué)旗幟”許淇。21歲發(fā)表于《人民文學(xué)》的處女作《大青山贊》,以大青山為地域符號(hào),將勘探隊(duì)員的故事與包頭青山區(qū)的命名淵源相勾連,既寫(xiě)地域風(fēng)貌,更頌時(shí)代建設(shè)者;《車(chē)馬大店》以?xún)?nèi)蒙古傳統(tǒng)驛站為切口,在新舊時(shí)代的對(duì)比中展現(xiàn)地域文化的變遷;散文《采風(fēng)記》聚焦內(nèi)蒙古民歌收集,字里行間浸透對(duì)本土文化的深沉熱愛(ài)。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:以強(qiáng)烈的地域辨識(shí)度叩開(kāi)全國(guó)性平臺(tái)的大門(mén),印證了“越本土越世界”的創(chuàng)作真理。
馮傳友從文化傳播視角補(bǔ)充道,地域性寫(xiě)作的生命力在于“根脈意識(shí)”。他以自己深耕包頭文化輸出的經(jīng)歷為例,在探討創(chuàng)作實(shí)踐時(shí),馮傳友以本土作家為例剖析地域性寫(xiě)作的尺度。他強(qiáng)調(diào):“地域性寫(xiě)作需避免冷僻方言,讓讀者既能觸摸到土地的溫度,又不被語(yǔ)言壁壘阻隔。”而詩(shī)人趙劍華以“鋼藍(lán)色”書(shū)寫(xiě)包鋼工業(yè)史詩(shī),張海魁《塞外皮毛商》深耕地方產(chǎn)業(yè)脈絡(luò),則證明地域元素可與時(shí)代精神深度融合,創(chuàng)作本身就是地域與歷史的鮮活注腳。
車(chē)夫提及本土作家如“水孩兒”等創(chuàng)作者,正是因?yàn)榫o扣腳下土地的肌理,才讓作品兼具地方特色與共鳴價(jià)值。車(chē)夫強(qiáng)調(diào),全球化時(shí)代的地域?qū)懽鞑⒎欠忾]的自我表達(dá),而是以本土為基點(diǎn),讓世界看見(jiàn)不同文化生長(zhǎng)的姿態(tài)。“只有扎根土地的莊稼才能成活。”車(chē)夫的比喻道破核心:當(dāng)?shù)厍虺蔀椤按迓洹保赜蛐圆皇莿?chuàng)作的枷鎖,而是讓文學(xué)擁有獨(dú)特質(zhì)感的靈魂。
地方故事也是世界注腳
在談及地域性寫(xiě)作的當(dāng)代價(jià)值時(shí),內(nèi)蒙古作協(xié)副主席、著名網(wǎng)絡(luò)作家張小花和內(nèi)蒙古作協(xié)原副主席、阿拉善文聯(lián)原主席張繼煉,結(jié)合自身創(chuàng)作實(shí)踐與本土文化觀察,對(duì)地域性寫(xiě)作的當(dāng)代價(jià)值展開(kāi)深入探討。
“只有扎根土地的莊稼才能成活。”張小花以這句質(zhì)樸的比喻,道出了地域性寫(xiě)作的核心意義。他在創(chuàng)作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(shuō)《史上第一混亂》時(shí),無(wú)意間融入“鋼鐵大街”“頂如”(包頭方言“相當(dāng)于”)等地域元素,讀者立刻從中辨認(rèn)出“包頭印記”。這種“藏不住”的地域特質(zhì),恰如魯迅筆下“濕漉漉的水鄉(xiāng)”、汪曾祺文中“高郵咸鴨蛋”,讓文學(xué)成為刻著土地年輪的靈魂載體。
張小花進(jìn)一步指出,網(wǎng)絡(luò)時(shí)代的讀者不會(huì)因“本土性”卻步:“就像東北文學(xué)復(fù)興,不必刻意寫(xiě)‘你瞅啥’,骨子里的地域精神藏不住。”
這一觀點(diǎn)在阿拉善作家張繼煉的實(shí)踐中得到印證。他以本土創(chuàng)作者為例提到:“曾有作家埋頭寫(xiě)阿拉善十幾年未突破,直到走遍云南、甘肅,在文化碰撞中才找到新靈感。”他呼吁作家既要深耕本土,更需“走出去”。只有寫(xiě)出土地的血肉,以及土地上人的精神,才算真正觸摸到地域文化的靈魂。
“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胎記,但需平衡運(yùn)用與讀者接受度。”張繼煉認(rèn)為,地域性寫(xiě)作的終極目標(biāo)是讓地方故事成為人類(lèi)共情的載體——正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(xiāng)、沈從文的湘西,包頭的“大青山”“鋼藍(lán)色”工業(yè)記憶,同樣在文學(xué)中突破地域邊界,獲得普世共鳴。
地域性不是創(chuàng)作的枷鎖,而是對(duì)抗文化同質(zhì)化的武器。用方言的韻律、土地的故事、時(shí)代的心跳寫(xiě)作,既是對(duì)文化根脈的守護(hù),更是讓地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生生不息的密碼——從許淇筆下的大青山到當(dāng)代作家的“鋼藍(lán)色”敘事,包頭文學(xué)的脈絡(luò)始終證明:真正的地域性寫(xiě)作,終將在世界圖景中留下屬于一方水土的鮮活注腳。
包頭市融媒體中心記者: 曹瑾,梁晶晶,祝家樂(lè);編輯:李寧寧;校對(duì)∶劉勇如;一審:尤允慶;二審:劉璟;三審:梁學(xué)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