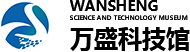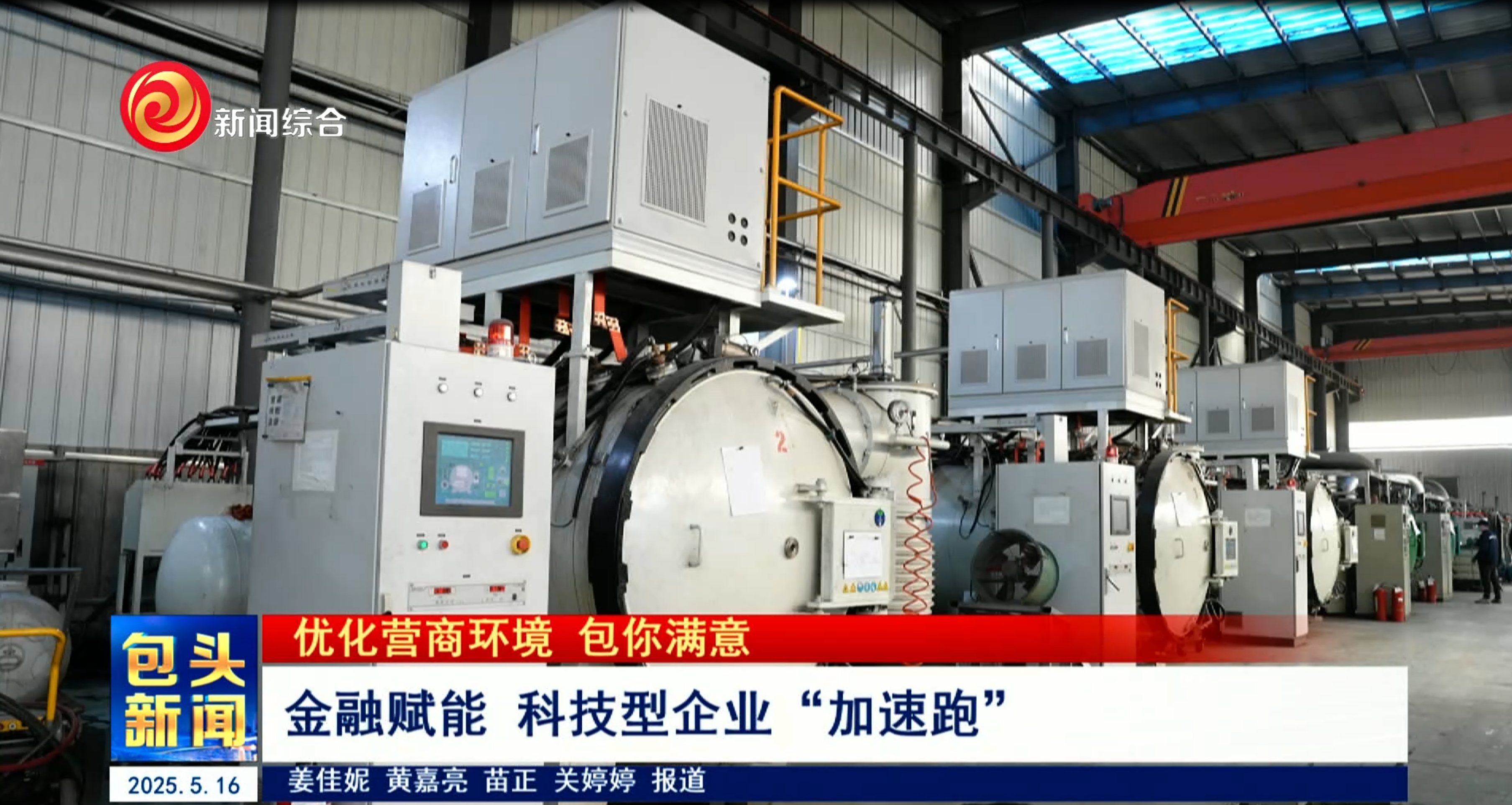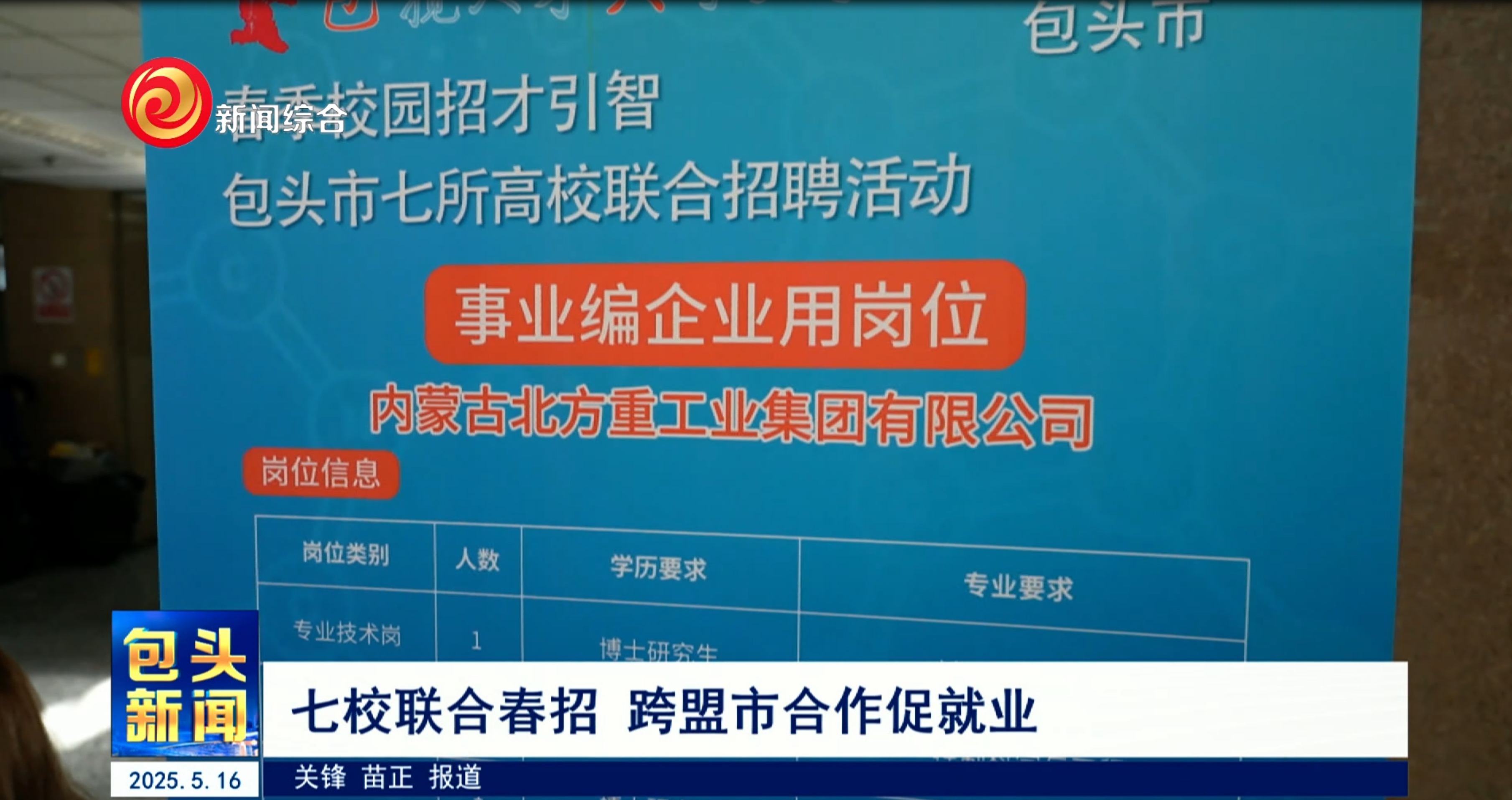趙永峰 攝
開欄的話
本土文學(xué),宛如這片土地上最悠揚(yáng)、最動(dòng)人的歌謠,它承載著我們共同的珍貴記憶,凝聚著我們深沉的情感,忠實(shí)記錄著時(shí)代的滄桑巨變與人民的煙火生活。今天,我們懷著無(wú)比崇高的敬意與滿腔熱忱,推出“經(jīng)典回響”這一全新專欄,精心為讀者們呈現(xiàn)本土名作家的經(jīng)典文章,讓這些歷經(jīng)歲月沉淀的文學(xué)瑰寶,再次于時(shí)光的舞臺(tái)上綻放奪目光彩。
這些經(jīng)典之作,恰似一面面鏡子,映照出包頭的精神風(fēng)貌與靈魂底色;又似一汩汩清冽的甘泉,靜靜流淌,滋潤(rùn)著我們干涸的心田,讓我們?cè)谛鷩碳姅_的塵世中,得以尋得一方寧?kù)o的綠洲,找到心靈的慰藉與歸宿。
——姬卉春

□許淇
即使冰凍的泥土也會(huì)被歲月焐熱,因?yàn)榍啻邯q如礦藏的潛能令春天永駐。
我雖然不是昆都侖河兩岸的拓荒者,但我是一名青年建設(shè)者。建設(shè)者,光榮的稱號(hào),讓人聯(lián)想到冰天雪地里保爾的形象和他那使整整一代人倒背如流的語(yǔ)錄。那時(shí)候,包頭團(tuán)市委辦的一張報(bào)紙就叫《青年建設(shè)者》。我負(fù)責(zé)編副刊《搖籃》,建設(shè)者的詩(shī)歌就在草原馬背上的“搖籃”里誕生。
我曾經(jīng)寫過(guò)《鋼鐵大街》,在《人民文學(xué)》上發(fā)表;寫到一個(gè)上夜班的老工人在鋼鐵大街上遇到一只狼。我曾經(jīng)寫過(guò)《人民日?qǐng)?bào)》的“名城賦”專欄,歌詠塞北這座新興的城市。
我曾經(jīng)參加包鋼高爐出鐵的慶典。我離主席臺(tái)很近很近,看見周恩來(lái)總理輕輕地有節(jié)奏地鼓掌。
我欣賞了馬連良先生的藝術(shù),不是在京都吉祥戲院或是津門滬上著名的大劇院,而是在包頭的昆都侖恰特,如今已顯得陳舊了,而當(dāng)年它卻是何等輝煌!
黃河岸邊的幾個(gè)村落,我吃過(guò)蒙古族鄉(xiāng)親們的酸撈飯。我居然在北方學(xué)會(huì)插秧和栽種水稻。修渠我唱自編的夯歌,拔麥子勒出個(gè)血手掌。在接近托克托縣的黃河邊,有一塊肥沃的河灘地,歸一名“知青”播種。他獨(dú)住在河邊小屋,晚間我躺在他的土炕上,聽他對(duì)著燈呱呱墜吹“枚”(笛),然后枕著寂寞的潮聲入夢(mèng),天還未亮,密集的湖鷗銳利的鳴唱喚醒了我……曾經(jīng)多少萍水相逢的人物和風(fēng)景呵!
北面的大青山和烏拉山我曾經(jīng)攀登,大樺背的樺林、九峰山的清澗,像一冊(cè)經(jīng)常耽讀的無(wú)名詩(shī)人的詩(shī)集。困難時(shí)期,為了逃避饑餓,市里有意組織干部到后山“秋收就食”,我們就以寫“公社史”的名義,心安理得地坐到莜面蕎麥豐收的老鄉(xiāng)們的炕桌上。在高山深處的耳沁堯,“跌死虼蛉碰死蛇”,當(dāng)?shù)谝惠v客車開到山村,我也不禁和那一輩子沒出過(guò)山的老娘娘一樣,噙著淚,撫摩了一遍又一遍……
呵,這一片熱土的角角落落都留下我的蹤跡。
最初我是個(gè)年輕的單身漢,不免有“江南游子”客居他鄉(xiāng)的相思,雙老健在,我每年必南歸省親。返回包頭,當(dāng)我扛著行李在車站下車,那漫天的風(fēng)沙和熟悉的方言,又喚起我本土方為“家”的強(qiáng)烈感覺。正如艾青在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中所說(shuō):“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!”作客在上海的亭子間和閣樓,我是什么也做不成,而這里卻有我的工作我的事業(yè)。待結(jié)婚成家、生兒育女之后,倦游歸來(lái),便見月臺(tái)上妻和小兒女迎接著,到家了!到家了!土居狹隘生活清寒,也有親切的笑語(yǔ),人間的溫馨,也有一爐好火、一杯薄酒,這就夠了!足夠足夠了!
每一道歷史的褶紋都刻印在我的臉上,每一陣政治風(fēng)云都波及我的朝夕,在這片熱土上,我個(gè)人的生活發(fā)生了許多故事,或可以說(shuō),什么都沒有發(fā)生;真不知從何說(shuō)起,或可滔滔不絕或竟是無(wú)話可說(shuō)。
如今不少土生土長(zhǎng)的年輕人,反而雛鷹高翔了。有的闖蕩到國(guó)外,在美國(guó)、日本,都會(huì)遇到包頭人,照樣別墅汽車,拿到綠卡簽證;有的到沿海地區(qū)當(dāng)白領(lǐng)“打工仔”,不甘做邊遠(yuǎn)地區(qū)的“鄉(xiāng)巴佬”,瀟瀟灑灑走一回。我老了,走不動(dòng)了,經(jīng)常寫信婉謝朋友的邀請(qǐng),年復(fù)一年地蟄居蝸角,視旅行若畏途,遠(yuǎn)方的地平線不再燃燒我信天翁式的渴望。雙老皆作古,原來(lái)的家鄉(xiāng)變得不可辨認(rèn),真正地陌生化了,于是我竟然說(shuō):咱們包頭人如何如何!我已和這方熱土融為一體了。
看來(lái)我的結(jié)局將不可避免……跨世紀(jì)的未來(lái)的人們呵,屆時(shí)請(qǐng)為我送行;一粒種子落歸大地之時(shí),我的靈魂才揚(yáng)帆起程,到一個(gè)很遠(yuǎn)很遠(yuǎn)的地方去……
許淇(1937—2016),當(dāng)代著名作家、書畫家。中國(guó)作家協(xié)會(huì)會(huì)員、一級(jí)作家,享受國(guó)務(wù)院政府特殊津貼。曾任包頭市文聯(lián)主席、《鹿鳴》主編、內(nèi)蒙古文史館館員、中國(guó)散文詩(shī)學(xué)會(huì)副會(huì)長(zhǎng)、內(nèi)蒙古作家協(xié)會(huì)名譽(yù)副主席。

□水孩兒
我在普救寺遇見了一只貓。
那是一只黃斑虎貓,很瘦,右腿上有傷,我踏入普救寺的那一刻它就認(rèn)出了我。
坐落于永濟(jì)市的普救寺,不僅是《西廂記》故事的發(fā)源地,更是無(wú)數(shù)情侶心馳神往的牽手打卡圣地。踏入普救寺,沿著蜿蜒而上的階梯前行,便能瞧見密密麻麻的同心鎖系在一旁。那些鎖,鎖住的是戀人們對(duì)愛情的美好祈愿,可不知為何,在某些瞬間,它們又像是無(wú)形的枷鎖,在講述著沒有后來(lái)的故事。
正欲拾級(jí)而上,冷不丁,側(cè)房屋檐上一只貓忽然竄到我跟前。它對(duì)著我“喵喵”叫起來(lái),那叫聲,仿佛帶著某種跨越時(shí)空的熟悉感,好似它已然認(rèn)出了前世的我。我每踏上一個(gè)臺(tái)階,它的聲音便愈發(fā)急切,圍繞著我不停地打轉(zhuǎn),看得出它想跳下屋檐靠近我,卻又帶著幾分畏懼,猶豫不決。我見狀,努力地伸長(zhǎng)手臂,試圖將它抱入懷中,然而指尖與它始終只差那么一點(diǎn)點(diǎn)距離,終究未能如愿。
望著這只貓,我不禁心生憐憫。它究竟經(jīng)歷過(guò)怎樣的過(guò)往?在前世,它又與我有著怎樣千絲萬(wàn)縷的姻緣呢?
想起前兩年,我在內(nèi)蒙古大學(xué)進(jìn)修,與青春洋溢的大學(xué)生們一同生活在校園里。每至畢業(yè)季,校園的角落里總會(huì)悄然出現(xiàn)許多流浪貓的身影。這些貓咪,大多是畢業(yè)后即將各奔東西的男孩女孩們無(wú)奈留下的。秋天的時(shí)候,陽(yáng)光透過(guò)斑駁的樹葉灑在草地上,那些流浪貓便在樹下尋覓著食物。它們或獨(dú)自徘徊,或三兩結(jié)伴,在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努力生存。
可是,嚴(yán)冬一到,凜冽的寒風(fēng)夾雜著紛飛的大雪席卷而來(lái),不少流浪貓沒能抵擋住這嚴(yán)寒,在冰天雪地中被無(wú)情地凍死。每當(dāng)回想起那些被雪掩埋的小小身影,我的心里總是涌起一陣酸澀。不過(guò),也有一些頑強(qiáng)的生命存活了下來(lái)。校園里善良的宿管阿姨們,于心不忍,便將這些可憐的小家伙收留在寢室門口。在阿姨們悉心的照料下,這些貓咪們有幸存活了下來(lái)。
來(lái)年春天,我驚喜地發(fā)現(xiàn),又有一窩一窩的小貓出現(xiàn)在校園的各個(gè)角落。它們?cè)诓莸厣湘覒颍诨▍查g穿梭,有時(shí)候也會(huì)偷偷被女生抱回寢室收養(yǎng)起來(lái)。但是秋天,它們又成為被遺落的青春碎片,在校園的角落里獨(dú)自承受著生活的風(fēng)風(fēng)雨雨。它們的存在,是對(duì)大學(xué)生們青春歲月的一種別樣見證,見證著他們的成長(zhǎng)、離別與無(wú)奈。
不管是普救寺的這只貓,還是內(nèi)蒙古大學(xué)那些流浪貓,它們都是生命長(zhǎng)河中的小小存在,在各自的環(huán)境里經(jīng)歷著生存的考驗(yàn)。普救寺的貓,在這承載著浪漫愛情傳說(shuō)的古寺中,或許也見證了無(wú)數(shù)情侶的悲歡離合。更或許,它本就是前世與我有過(guò)一段情感糾葛的某個(gè)人呢?
站在普救寺的階梯上,我再次望向那只貓。它依然在屋檐上徘徊,那叫聲像是在呼喚走失已久的戀人。
我看著它,忽然想起衣袋里有一袋奶酪,便掏出來(lái)放在掌心,盡力向前遞去。它的雙爪踩在屋檐的瓦片上,努力伸出舌頭,一下一下地舔食起來(lái)。它的舌頭粗糙,刮得我手心發(fā)癢。
同行的友人笑問:“它認(rèn)得你嗎?”
“不認(rèn)得吧!”我答:“也許它只是餓了。”
友人笑笑,說(shuō):“可是它好像只認(rèn)你。”
我不置可否。想起那些同心鎖,想起校園里的貓,想起生命里來(lái)了又走的人。愛情大約也是如此吧,以為是獨(dú)一無(wú)二的相遇,其實(shí)不過(guò)是又一次重復(fù)的乞討與施舍。
奶酪吃完了,那貓仍不肯走,在我頭頂?shù)奈蓍苌吓腔病N已鲱^看它,它低頭看我,彼此都有些不甘心。我想抱它下來(lái),卻又夠不著;它想再討些水喝,卻又下不來(lái)。僵持了一會(huì)兒,我終于狠下心來(lái)轉(zhuǎn)身,向著普救寺的塔頂?shù)侨ァ?/span>
或許,它只是偶然間對(duì)我產(chǎn)生了好奇,而我卻賦予了它如此多的遐想。但這又何妨呢?在這瞬息萬(wàn)變的世界里,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相遇與聯(lián)想,正是生活給予我們的獨(dú)特饋贈(zèng)。
陽(yáng)光下的普救寺依舊靜靜地矗立著,迎來(lái)送往著一批又一批的游客。
我離開普救寺時(shí),那只貓又出現(xiàn)了。它躲在門口的石墩后面,遠(yuǎn)遠(yuǎn)地望著我。我向它揮揮手,它叫了兩聲,便轉(zhuǎn)身跳下石墩,消失在寺廟中。我想,它大約是怨我狠心離開了,又大約是在等待下一個(gè)手里有奶酪的游人吧。
同心鎖在微風(fēng)中輕輕搖曳,發(fā)出清脆的聲響。仿佛在訴說(shuō)著什么,又仿佛只是被風(fēng)吹動(dòng)了而已。

□周靜
五一小長(zhǎng)假,幫母親整理衣柜時(shí),我發(fā)現(xiàn)一件眼熟的粉色坎肩。
“這不是我那件十幾年前的外套嗎?”我問母親。母親慢悠悠地說(shuō):“我把它改成坎肩了。”母親已到了古稀之年,對(duì)縫縫補(bǔ)補(bǔ)的熱度依然不減當(dāng)年。
母親出身貧苦人家,只讀過(guò)兩年書的她很能吃苦,從小就幫家里干活,洗衣做飯、納底做鞋、鋤地割草,家里家外一把“好手”。心靈手巧的她年輕時(shí)跟村里的老師傅學(xué)過(guò)裁縫。二十一歲時(shí)成家后,每天與父親早出晚歸,耕田種地。
等有了我和弟弟,母親白天就更忙了,只有晚上她才能閑下來(lái)做針線活。昏黃的煤油燈下,母親總是低著頭,隔一小會(huì)兒,會(huì)把帶著長(zhǎng)長(zhǎng)絲線的針在頭發(fā)上擦一擦,再去縫制衣服,如此反復(fù)。到了冬天,我們姐弟倆趴在鋪著油布的炕上寫作業(yè),母親就坐在我們旁邊縫補(bǔ)衣服。冬天的夜漫長(zhǎng)又寂靜,寫完作業(yè)的我們,早早就鉆進(jìn)暖和的被窩里。母親卻仍在煤油燈下穿針引線,那一下接一下的“嚯嚯”聲,在寒冷的夜晚顯得溫暖又甜蜜。
幾年后,生活稍稍好了一些,父親托人從外地買了一臺(tái)前進(jìn)牌縫紉機(jī)。母親高興極了,滿眼含笑,不停地打量著這臺(tái)渴望已久的縫紉機(jī),用她那粗糙的手摸摸這兒、摸摸那兒,如同獲得了一件稀世珍寶。自從家里有了縫紉機(jī),母親做針線活再也不用發(fā)愁了,改衣服、縫新衣的效率高了,夜里縫紉機(jī)“噠噠”聲持續(xù)時(shí)間也更長(zhǎng)了。
小孩子總是長(zhǎng)得特別快,頭一年穿著還算合身的衣服,到了第二年就短了一大截。母親的手藝有了大用場(chǎng),她一會(huì)兒用尺子量一量,一會(huì)兒用剪子剪一剪,一會(huì)兒又坐在縫紉機(jī)前,左手捏住布料,右手旋轉(zhuǎn)機(jī)輪,雙腳勻速踩動(dòng)踏板,布料沿著針頭緩緩前行。工夫不大,又小又短的衣服就“變”大了。我們姐弟倆穿著母親縫制的“新衣服”在村里四處瘋跑,如果被愛美的孩子和村里的大嬸們看到,接下來(lái)我家肯定會(huì)熱鬧好幾天。
印象最深的是母親為我做的花格子書包。布料是母親從剩下的花布頭上剪下來(lái)的,方方正正,花花綠綠。然后用縫紉機(jī)一塊連著一塊拼接縫合而成,既結(jié)實(shí)又好看,正好裝下我的課本和鉛筆盒。我斜挎著花格子書包去上學(xué),心里別提有多高興了,連路邊的花兒草兒似乎也在跟著我一起跳躍。同學(xué)們投來(lái)羨慕的目光,我便更加得意,仿佛那書包里裝的不是書,而是某種榮耀。那是母親所期盼的一種“榮耀”。
后來(lái)我當(dāng)了老師。學(xué)校舉辦30周年校慶活動(dòng),要定做一批桌套。校長(zhǎng)得知母親學(xué)過(guò)裁縫,便把這差事交給了母親。那段日子,家里堆滿了藍(lán)色的布料,空氣中飄著新鮮的棉布?xì)馕丁D赣H從早忙到晚,常常顧不上吃飯。夜深了,縫紉機(jī)仍不時(shí)傳來(lái)有節(jié)奏的聲響,時(shí)而急促,時(shí)而緩慢,伴我進(jìn)入夢(mèng)鄉(xiāng)。校慶那天,全校課桌都“穿上”了母親做的藍(lán)桌套,齊齊整整,成為教室里一道亮麗的風(fēng)景。當(dāng)我走進(jìn)教室,望著這些格外鮮亮的藍(lán)桌套,心里涌起一種莫名的自豪。
再到后來(lái),我們都成家了,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母親就親自給孫子、外孫做衣服,在她看來(lái),買的衣服遠(yuǎn)遠(yuǎn)不如她自己縫的舒適、放心。
歲月流逝,母親老了,眼睛也花了。可她放不下那臺(tái)縫紉機(jī),仍舊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計(jì),至今家里還有母親給我們?nèi)铱p的棉拖鞋和鞋墊。母親還會(huì)突發(fā)奇想,將舊外套改成馬夾、半袖改成背心,甚至還會(huì)做八角帽……每次都會(huì)高興地給我分享她的“杰作”。
近些年,母親身體大不如前,終于不得不與縫紉機(jī)告別。賣掉它的那天,母親坐在陽(yáng)臺(tái)的椅子上,久久地望著那個(gè)空出來(lái)的角落。在母親眼中,那絕非一塊空蕩蕩的地板,而是四十多年來(lái)在縫紉機(jī)前度過(guò)的日日夜夜——那些為家人縫制的衣物、那些為生計(jì)趕工的辛苦、那些將愛意縫進(jìn)一針一線的時(shí)光……

□漠津
父母的愛子之情中有喜愛小貓小狗般輕佻的成分,愛其嬌弱溫順。當(dāng)孩子漸生出意志和自尊,這部分喜愛便會(huì)急劇消退。這是女兒毛豆三歲半時(shí)我個(gè)人的觀察和體驗(yàn)。
起初,我是在愛人春雪的身上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一端倪。
曾經(jīng)春雪是一個(gè)為滿足毛豆需求不顧后果的母親。我們推著嬰兒車穿過(guò)一個(gè)繁忙路口的非機(jī)動(dòng)車道時(shí),毛豆大哭,春雪不顧來(lái)往密集車流,當(dāng)即將一米多長(zhǎng)的嬰兒車橫置車道正中,屈身為毛豆更換紙尿褲,右轉(zhuǎn)的電動(dòng)車紛紛急剎、擁堵一團(tuán),甚至將占用輔道右轉(zhuǎn)的機(jī)動(dòng)車都擠到了主道上。一時(shí)漫罵鳴笛聲大作,春雪如夢(mèng)初醒,才將嬰兒車推到一步之遙的人行道上繼續(xù)伺候毛豆,壓根沒意識(shí)到自己方才的舉動(dòng)多么危險(xiǎn)荒唐。毛豆未滿周歲時(shí)睡覺極輕,我們便不敢在午夜孩子熟睡前如廁,深恐沖廁聲驚擾毛豆再生事端。
好像一條臍帶仍然連接著母女,孩子的痛苦會(huì)成倍地放大于春雪之身,將她變作了一具喪失理性和自主意志的傀儡。她將自己作為母親的嚴(yán)苛標(biāo)準(zhǔn)套用到我和毛豆奶奶身上,許多難解的積怨因此萌生。彼時(shí)我一大心愿就是,春雪能脫離毛豆的操控,稍稍寬待自己和我們。這個(gè)愿望在毛豆兩歲半左右實(shí)現(xiàn)了。一日,春雪刷著抖音再三掙脫孩子不得,忽然厲聲吼道:“你就不能自己玩一會(huì)兒!”
方才還張牙舞爪的毛豆被這聲怒喝定在了原地,活像深夜被突來(lái)強(qiáng)光嚇破膽的貓頭鷹,縮著脖子瞪著春雪,乍著雙手,嘴巴呷著黃連般苦澀地一張一合。被她瞪惱的春雪喝問:“你瞪誰(shuí)呢?”毛豆戰(zhàn)栗,從驚愕中清醒,撇著小嘴爬下床,光腳踩地的咚咚聲深入毛豆奶奶的臥室,隨之傳來(lái)輕聲乖哄和委屈的悲哭。
毛豆被呵斥之后的呆樣與我兒時(shí)一模一樣。
據(jù)毛豆奶奶所說(shuō),我幼年常遭醉酒父親的恫嚇、掌摑與踢踹,又總是目睹家中頻起的紛爭(zhēng),所以在遭到粗暴對(duì)待時(shí),會(huì)呆立原地、直勾地盯著對(duì)方。老師訓(xùn)斥我時(shí)總以為那呆瞪、是在挑釁,耳光、書本便劈頭蓋臉砸來(lái)。毛豆奶奶向老師解釋,這是因我被父親的喜怒無(wú)常刺激所致。然而,她在我脊背上砸斷過(guò)幾根抓撓、終日諷刺我魯鈍懶散的往事,她絕口不提。
自那事之后,春雪帶頭摧毀了由她自己建立的嚴(yán)格的育兒標(biāo)準(zhǔn),對(duì)毛豆的需要漸漸漫不經(jīng)心。我亦順勢(shì)躲清閑,除非媽媽、奶奶皆不理睬,毛豆才會(huì)蹭到我身邊小聲問:“一起玩?”若被拒,她便摟緊布娃娃“貓頭”、叼著水壺蜷縮床頭等待睡意降臨。
直至上園,毛豆忽然在午夜頻頻尿床或嗆水大哭,我們數(shù)日不得安眠、終日頭昏腦脹,但她仍然拼命捍衛(wèi)自己喝水入睡的習(xí)慣。那晚毛豆又大哭,我感到那道厲聲劈中了墻面又連同混凝土的碎屑彈進(jìn)了我的耳廓,刺得我耳膜生疼、嗡聲陣陣。
我從枕上彈起,一連三個(gè)巴掌打在毛豆額角至后腦勺的位置,聞聲趕來(lái)的毛豆奶奶打開燈,娃娃正坐在床上死死地拽著小背心尖叫,又拼命克制著自己哭嚎,兩股劇烈頂撞的力量讓她渾身顫抖、打著嗝抽噎,像只即將頂開蓋的沸騰水壺。毛豆奶奶伸手要抱,毛豆直直地伸出胳膊,并攏五指拒絕了乖哄,獨(dú)自吞咽著一切。
父母打孩子的動(dòng)機(jī)無(wú)數(shù),可理由只有一個(gè),成人可以用暴力懲罰幼兒帶來(lái)的不快,孩子無(wú)力反過(guò)來(lái)做。再厚重的愛也難抵這種不對(duì)等產(chǎn)生的肆意妄為,這是親子關(guān)系的一層本質(zhì),其表現(xiàn)貫穿了我的童年,也終于在毛豆的生命中初現(xiàn)征兆。
想起之前,我陪著未滿周歲的毛豆午睡,娃娃的柔軟鼾聲如煮沸牛奶的蒸汽氤氳在整個(gè)房間,小嘴、臉蛋、腦門肉嘟嘟地高高隆起,像只蘭壽金魚在溫煦的日光中吐泡泡,我單手撐頭側(cè)臥在榻榻米上昏昏欲睡,毛豆抱著布娃娃咕嚕一下滾入我的懷中,小嘴吧咂著發(fā)出“巴咕巴咕”的聲音。那一刻,幸福的震顫似轟擊,又似刺痛,我?guī)子箿I。我想,我會(huì)愛這個(gè)孩子,會(huì)以與我父母完全不同的方式愛這個(gè)孩子。
我錯(cuò)了,愛孩子,同時(shí)保持對(duì)暴力的高度警覺也并不能讓我成為一個(gè)好父親。
這究竟,是怎么回事呢?
那晚,毛豆拒絕大人乖哄的戲劇化姿態(tài)讓我印象尤深,這種倔強(qiáng)顯現(xiàn)出天生的內(nèi)在力量。毛豆一定會(huì)比至今仍在童年泥淖中掙扎的我更加強(qiáng)大。
我努力溫柔一些,毛豆堅(jiān)強(qiáng)一些,我們的未來(lái),會(huì)比我的過(guò)往更臨近幸福,我如此希望,我這樣相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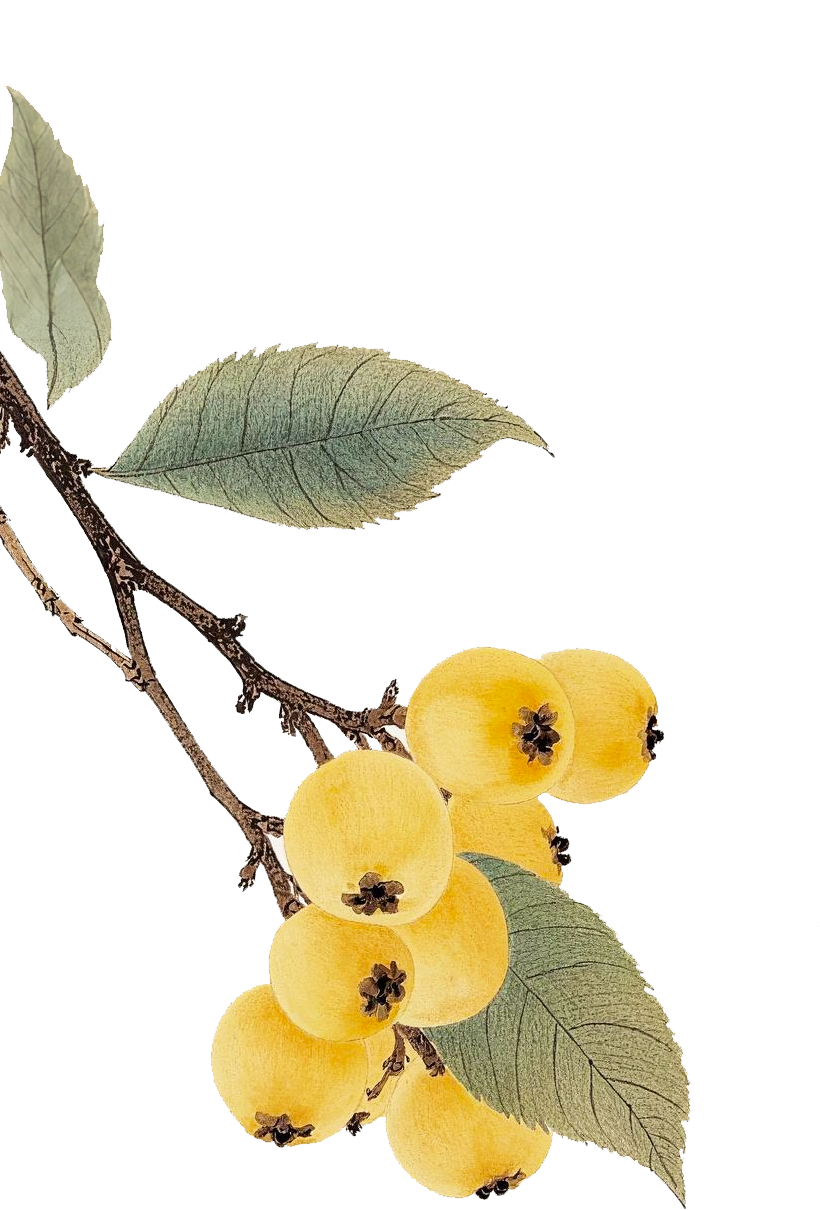
□李春
雨如精靈
焦渴了一個(gè)季度
相思的淚
沖破了浩渺的時(shí)空
跌落在思念的河床上
寒冬的那頭
似曾有過(guò)飛逝的紅顏
大地
蘇醒了刻骨銘心的癡情
北方的初春
不喜歡煙雨江南的溫柔
雨露桃花
撐開了素默的胸口
雨落春天
草也長(zhǎng)
鶯也飛
夢(mèng)的花朵
悄然開放
所有的播種
都能芬芳嗎
眺望田野
叩問汗水
攜手陽(yáng)光明媚的日月
種一片風(fēng)光
秋日里
我們一起聽蛙聲連奏
稻花香里
笑揮銀鐮

(編輯:吳存德;校對(duì):霍曉霞;一讀:張飛、黃韻;一審:張燕青;二審:賈星慧;三審:王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