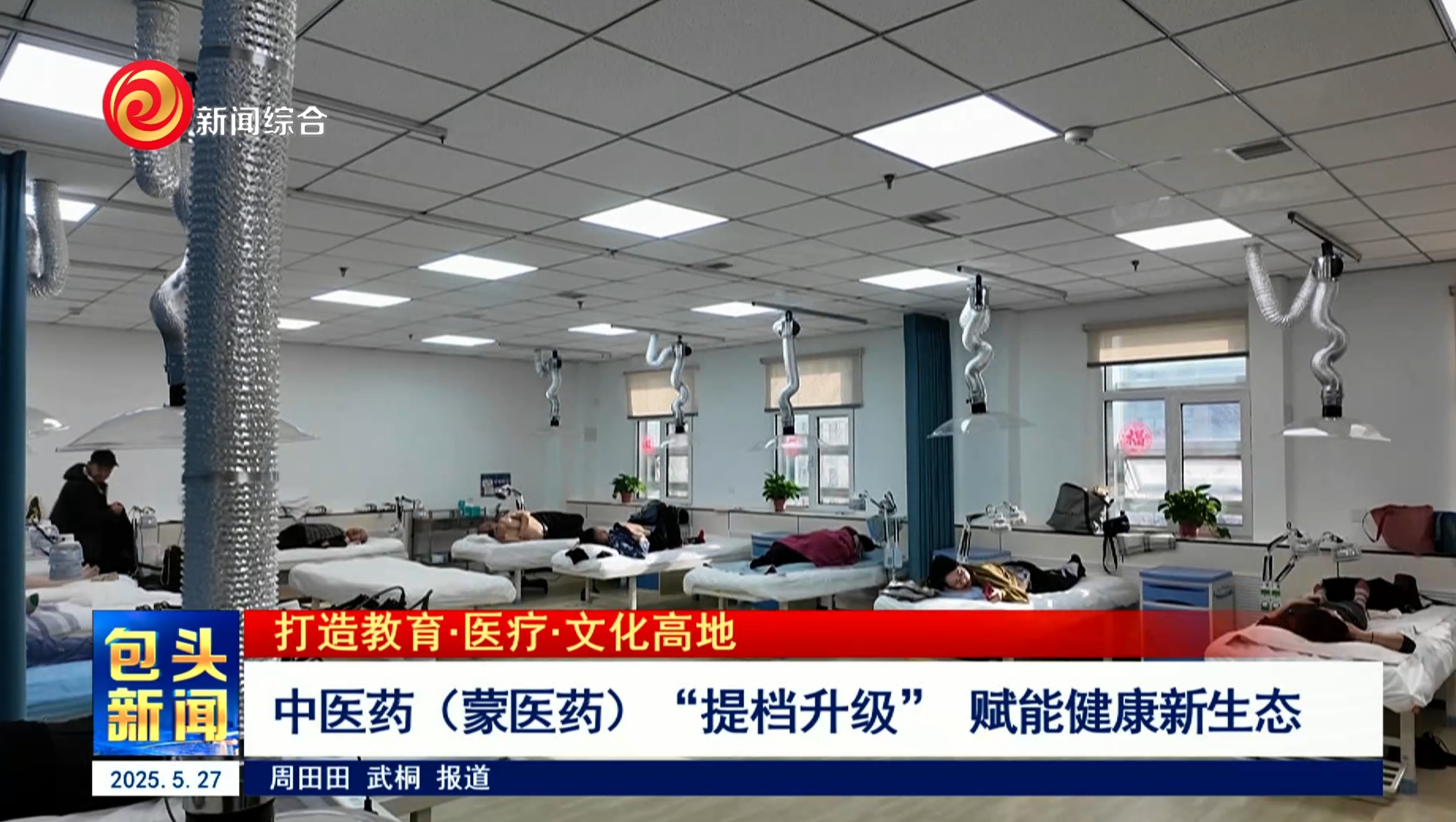老舍說:“人,即使活到八九十歲,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。失了慈母,便像花插在瓶子里,雖然還有色有香,卻失去了根。有母親的人,心里是安定的。”
麥兜的媽媽說:“全世界的人不信你,我也會信你;全世界的人不愛你,我也會愛你。我愛你愛到心肝里,我信你信到腳趾頭。”
——策劃 姬卉春
 趙永峰 攝
趙永峰 攝



□劉東華
暮春的風(fēng)裹著紫丁香的甜香漫進窗欞,我望著枝頭簇擁的花苞,恍惚間又回到了那些飄著麥香的清晨。
灶臺上蒸騰的熱氣里,姥姥布滿老繭的手翻動著茴香餅;昏黃的臺燈下,媽媽戴著頂針的手指在布料間穿梭。歲月將往事釀成陳酒,每當(dāng)某個相似的場景浮現(xiàn),記憶便會沖破時光的封印,帶著溫暖的余溫重新流淌。
那年我剛滿十歲,蟬鳴還未響起,媽媽卻永遠留在了料峭的五月。她因病住院,身體已經(jīng)虛弱得無法久坐,卻仍堅持坐在病床上為我縫制新衣。淡粉色的確良布料在她膝頭鋪開,像一片溫柔的云霞。她戴著老花鏡,用微微顫抖的手穿針引線,領(lǐng)口處的雛菊繡得格外用心,鵝黃的花蕊是用最細的絲線一點點勾勒,在陽光下泛著珍珠般的光澤。
“等繡完這只小貓,等夏天來了……”她總這樣喃喃自語,可命運卻沒能給她完成的機會。最后的日子里,她連握針的力氣都沒有了,未完成的衣裳靜靜躺在針線筐里,衣襟下方的貓咪只繡了半只爪子,仿佛永遠定格在撲向毛線球的瞬間。葬禮那天,我偷偷把這件衣裳疊好放進書包,貼著心口的位置,仿佛這樣就能留住媽媽最后的溫度。
媽媽走后,堅強的姥姥擔(dān)負起了照顧我的責(zé)任。某個清晨,我被槐樹枝椏間的鳥鳴喚醒,推開門看見姥姥正坐在老槐樹下編竹篾。陽光穿過樹葉的縫隙灑在她身上,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。
“來幫姥姥扶著竹條。”她笑著招呼我。竹篾在她手中像被賦予了生命,三彎兩繞就成了風(fēng)箏的骨架。我看著她靈巧地糊上宣紙,用彩筆勾勒出燕子的翅膀,墨汁未干時,她就把風(fēng)箏系在我手腕上:“逆著風(fēng)跑,風(fēng)箏才能飛得高。”那天的風(fēng)很大,我舉著燕子風(fēng)箏在田埂上奔跑,身后傳來姥姥略帶沙啞的笑聲,混著遠處的蛙鳴,成了童年最動聽的樂章。
姥姥的手仿佛有魔法。秋天的玉米秸稈在她手里能變成會旋轉(zhuǎn)的風(fēng)車,枯黃的蘆葦葉能折成蹦跳的螞蚱。寒食節(jié)時,她會在面團里摻進菠菜汁,捏出的寒燕栩栩如生,翅膀上還點綴著紅豆做的眼睛。過年時,她佝僂著背在案板前忙碌,搟出的餃子皮薄如蟬翼,包出的元寶餃個個挺著圓鼓鼓的肚子。我總愛趴在廚房門口看她,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,和媽媽的身影漸漸重疊。
時光悄然流逝,轉(zhuǎn)眼間我的女兒也到了四年級。那天放學(xué)回家,她興奮地舉著一張畫:“媽媽,這是我畫的全家福,等我長大了,要帶你們?nèi)タ凑嬲拇蠛!!碑嬂锿嵬崤づさ男∪耸掷郑屛蚁肫鹦r候依偎在姥姥和媽媽中間的日子。可命運總是猝不及防,那個春天,姥姥也因病離開了。
整理遺物時,我在樟木箱最底層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藍花布包。打開的瞬間,淚水模糊了視線——里面整整齊齊疊著我小時候的衣裳,媽媽未完成的粉色上衣被重新包上了邊,針腳細密得看不出新舊。原來在我看不見的時光里,姥姥用她的方式延續(xù)著媽媽的愛。
今年母親節(jié)前夕,在外地讀大學(xué)的女兒寄來了一份特別的禮物——一把符合人體工學(xué)的椅子。視頻里,她紅著眼圈說:“媽,自從你去年閃了腰,受累受凍后總說腰疼,這個椅子能保護你的腰。”我摸著椅面柔軟的皮質(zhì),突然想起小時候媽媽也是這樣摸著我的頭說“別凍著”、姥姥也是這樣握著我的手說“慢慢走”。
雖然我沒能學(xué)會姥姥的一手好廚藝,也不像媽媽那樣擅長女紅,但我學(xué)會了用另一種方式傳遞愛。女兒備戰(zhàn)高考時,我每天凌晨四點起床熬銀耳羹;她第一次離家求學(xué),我背了滿滿一書包她愛吃的零食去送她上學(xué)。這些瑣碎的日常,何嘗不是愛的延續(xù)?
窗外的紫丁香開得愈發(fā)濃烈,恍惚間,我仿佛看見三代人圍坐在老槐樹下:姥姥在教媽媽繡雛菊,媽媽在給我扎風(fēng)箏,我正握著女兒的手教她包餃子。時光帶走了容顏,卻讓愛愈發(fā)醇厚。原來母愛從來不是單向的付出,而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接力,在一針一線、一粥一飯中代代相傳,溫暖著生命的每個瞬間。





□張偉
赤峰的冬天很冷。干打壘的土平房,室內(nèi)山墻上掛著厚厚的一層霜雪。沒有煤炭,灶膛里燒的是莊稼秸稈,前半夜炕頭還是熱乎的,后半夜就涼透了,早晨更冷。
母親起得早,給我們做早飯。在東北農(nóng)村,早飯和午飯、晚飯一樣,是整頓飯,而不是意思一下的早點。飯做好了,母親把灶膛里的火鏟到火盆里,把火盆端到屋里,頓時暖騰騰的。這時,母親倒提著我棉褲的兩只褲腳,在火盆上烤,烤熱了,再叫我起來,給我穿棉褲。一邊穿,一邊嘴里叨咕著“窩啦窩啦窩啦”。就這樣,在冰冷的屋子里,我愉快地穿好衣服,吃早飯。這份溫暖,來自火盆,更來自母親的悉心關(guān)愛。
在村子里,母親絕對是個“人物”。婆媳勃溪,妯娌矛盾,鄰里糾紛,常常會來找母親,請她出面調(diào)解。母親也總是很熱心,撂下家務(wù)事兒,一趟又一趟地去給說和,兩頭做工作,化解紛爭,大事化小,直至捐棄前嫌,和好如初。
農(nóng)村是排外的,有個搬遷戶,被坐地戶欺負,女主人受刺激,神經(jīng)錯亂了。母親很同情她,好言相勸,寬慰的話說了一簸籮,一次不通,就兩次,還給她送好吃的。終于,母親幫助她走出了心理陰霾,恢復(fù)了正常,忙忙叨叨地過起了莊戶人的日子。
母親好口才,很擅長做勸解工作。能根據(jù)不同人的不同性格、不同心理,對癥下藥,藥到病除。我能把課講好,是有得自母親的強大基因的。
按照鄉(xiāng)間的風(fēng)俗,娶媳婦要請娶親婆。這個角色,不是誰都能扮演的。得兒女雙全、家里面全全整整的,公認的有福之人。這也好理解,沒別的,圖個吉利吧,托娶親婆的福,把美好、幸福帶給新人。當(dāng)然,還得是場面上的人,能說會道,處理娶親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意外,用現(xiàn)在的專業(yè)術(shù)語說,就是具備危機公關(guān)的能力。
母親經(jīng)常被請去給人娶親。坐著馬車,到女方家,吃一頓飯,把新媳婦娶回來。下車時,是很有儀式感的。搬一張八仙桌放在右車耳下面,娶親婆、新媳婦下車時,腳落在八仙桌上,而不是撲騰一聲跳到地上。進了屋,要擺放炕桌,請娶親婆和女方送親的客人吃點心。沾母親的光,我也享受過這樣的禮遇。看見娶親的車回來了,就會有一個姐姐把我送過去,坐在母親身邊,吃我最愛吃的糖棗啊、桃酥啊、大餅干啊,平時難得吃到,一飽口福。
母親很能干,印象比較深的是她帶著我們挖樹根。樹伐倒了,樹根留在地下,挖出來,可以當(dāng)柴燒。我們的說法,叫挖樹疙瘩。這個活兒很不好干,盤根錯節(jié),處處是障礙,鐵锨、斧頭并用,一兩個小時過去了,還是沒有多少進展。那時母親已經(jīng)不年輕了,還把自己當(dāng)成壯勞力,擺開架勢,要大干一場。樹根挖出來,晾干,劈成小塊的劈柴,整整齊齊碼放在院里。其實,有父親的一份收入,又沒有那么多等著娶媳婦、需要支付彩禮的男孩,不必這么辛苦。但母親和別人家一樣,一針一線,一枝一葉,勤儉持家。
高考錄取通知書來的那天,站在西屋地上,我在墻上很大很大的中國地圖上指出包頭所在的位置,母親的眼淚嘩地流了出來。沒上過學(xué)的母親,哪里懂得比例尺,哪里知道赤峰到包頭的實際距離,她只覺得兒子要離開家了,要離開她了,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了,既為我考上大學(xué)而高興,又是那樣的不舍和無奈。
母親離世時,我不在身邊。母親去世的噩耗傳來,緊趕慢趕往家趕。趕到時,母親的靈柩已在墓地,釘住棺蓋的那顆陰陽兩隔的大釘子還沒有釘上,就是為了讓我看母親最后一眼。
“父母在,不遠游。”我沒能做到。按照老祖宗的倫理,這已是不孝。接下來的一句,“游必有方”,算是不孝之子為自己開脫的托詞了。我遠在外地,始終拼盡全力,想成為父母眼中的驕傲,也唯有如此,方能稍稍撫平心中的那份愧疚。


趙永峰 攝



□王艷
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生的父母輩,大多數(shù)家庭物資匱乏,生活艱辛,經(jīng)歷坎坷。母親也一樣。
如今七八十歲了,雖有點健忘,剛說的話會再重復(fù)一遍,剛放起來的東西轉(zhuǎn)頭就不知道放哪了,但母親身體很硬朗,精神頭十足,總也閑不下來。除了照顧父親的飲食起居,春天撿樹枝、夏天割羊草、秋天拾玉米、冬天腌酸菜,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,忙碌著,快樂著。
東北的春天,大風(fēng)三天兩頭地刮,在無遮無攔的遼西大平原上肆虐。平原上的防護林多是楊樹,防洪溝畔,田間地頭,到處都是,防風(fēng)固土。每年春天,除了人工修剪,大風(fēng)也會給楊樹來一次自然界的修剪。
東北睡火炕,樹枝燒炕,熱得快、蓄熱久,是很好的柴火。母親的口袋里時常裝著手套、麻繩,天天盼著刮大風(fēng),時時等著撿樹枝。今天到東面的河溝沿上撿,明天去西邊的河溝沿上撿。撿得少,就自己用推車推回家;撿得多,就讓二妹用三輪車拉。撿回來的樹枝齊整整地碼在院外,仿佛列隊的士兵。我每次回去,母親都會像將軍檢閱部隊一樣,從柴火垛前慢慢走過,并一一指給我:“這些是今年春天撿的,那些是去年春天撿的……”竟還有三四年前的,舍不得燒,用得很節(jié)省。我老說她,家里又不缺柴火,撿那東西干啥,又臟又累的,別再摔上一跤。她不聽勸,轉(zhuǎn)頭又去了。年紀大的人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證明自己還有用,也是一種情緒的寄托。理解了她的需求,我也就釋然了,就陪她一起撿。
夏天到了。生了三個閨女的母親和二妹一起生活。二妹家養(yǎng)了三只羊。夏天,為了能讓羊吃上新鮮的嫩草,母親每天都要給這三小只去割草。今天去這個田間地頭,明天去那個溝溝畔畔。夏天的下午,兩三點鐘是日頭最足的時候,她也經(jīng)常不休息,偷偷出去割羊草。二妹也很無奈。有時候父親擔(dān)心她一個人背不動,就開動上輪椅,陪她一起去,給她做個伴。母親把割下來的羊草裝在袋子里,系在父親的輪椅上,相跟著一起回來。每當(dāng)母親從小羊身邊經(jīng)過,三小只都會伸長了脖子,歡快地叫著,期待著美味大餐。聽二妹說前幾天又買了兩只羊,看來今年夏天,母親要更忙了。
老家黑山縣是農(nóng)業(yè)大縣,農(nóng)作物主要是玉米。秋天的千里大平原,一望無際的金黃。收割機過后,總會有“漏網(wǎng)之魚”。把這些遺留在地里的玉米一個一個拾起來,東北話叫撈(讀四聲)苞米。現(xiàn)在農(nóng)村也富了,沒人在乎丟下的那幾個玉米,特別是外出打工的人,匆忙回來,收完就走,幾乎沒有幾個人去仔細地翻找。
但母親有的就是時間。她幫二妹把自家的玉米收完、撈完,就到別人家的田里去撈,最多的時候一天能撿五六十斤。出去遛彎,也不忘手里拿個塑料袋,這兒瞧瞧那兒看看,總會撿回來幾個。母親自豪地說,去年秋天她一個人撈了1000來斤,夠雞和羊吃好一陣子的。我陪她在村邊的小路上散步的時候,她就會反復(fù)地指給我:在這塊地里撈過多少,在那塊地里撈過多少。談?wù)撨@些時,我看到了母親眼里的光。
東北的酸菜色澤金黃,酸溜溜,脆生生,無論是物資匱乏的年代,還是美食豐富的今天,都是東北人餐桌上的常客。東北人對酸菜都有著近乎瘋狂的摯愛,酸菜燉豬肉、酸菜燉粉條、酸菜汆白肉、涼拌酸菜心、酸菜餡餃子……做法五花八門,百吃不膩。
立冬過后,家家開始腌酸菜。母親也要親自挑選自家種的大白菜,腌上兩大缸。選好的大白菜去老幫,切根洗凈,直接碼入大缸中,一層大粒鹽一層大白菜直到缸滿為止,再用重石壓上,待兩天之后白菜下沉加入清水,將缸口用缸蓋封好,等待發(fā)酵,一般三十天左右才能食用。
菜腌好了,母親就開始念叨,今年大閨女能回來過年不?我最愛吃的就是酸菜蒸餃,再配上醬油蒜泥,那味道瞬間喚醒小時候?qū)业挠洃洝N颐看位丶遥紡埩_著給我包酸菜餡餃子。熱氣騰騰的酸菜蒸餃端上桌,全家圍坐在一起,吃著聊著,紅火熱鬧,那份溫暖與幸福,是任何山珍海味無法替代的。
吃母親腌的酸菜,睡在有母親的熱炕頭,一遍遍地聽母親嘮叨她撿樹枝、割羊草、撈玉米、腌酸菜的故事,心里特別的踏實與滿足。
《百年孤獨》里說:“人的精神寄托可以是音樂,可以是書籍,可以是工作,可以是山川湖海”。春天撿樹枝、夏天割羊草、秋天撈玉米,冬天腌酸菜,就是母親的四季、母親的精神寄托、母親生活的樂趣,簡單而執(zhí)著。





□李春燕
合上書頁,敬一丹在《床前明月光》里對母親的追憶如潮水般漫過心間,那些細膩的文字,輕輕叩擊著我內(nèi)心最柔軟的角落。泛黃的紙頁間流淌的不僅是文字,更是千萬個與母親有關(guān)的瞬間,在記憶的長河里泛起層層漣漪。
母親與我,是血脈相連的母女,卻又好似是上一世就已結(jié)下的緣分,不然,為何在茫茫人海中,我們能如此緊密地依偎在一起,共度這一世的時光?這份緣分從那個驚心動魄的清晨便已注定。
數(shù)年前,母親曾笑著向我講述那段往事。那一年臨近春節(jié),夜晚母親突然感到腹部傳來撕裂般的疼痛。父親慌亂地沖出家門找車,可還沒等車回來,我便急不可待地降臨人間。家中的桌子鋪上棉被,鄰居楊奶奶臨時充當(dāng)接生婆,母親獨自承受著生死考驗。那是何等的痛苦,一個人從一個人身上剝出來。母親滿臉笑容回憶往事,我卻早已禁不住淚水漣漣,我是母親用命換來的禮物。
從那以后,我對生日有了別樣的情愫。每年這一天,我不再熱衷聚會慶祝,而是特意推掉所有安排,只為與母親單獨度過。我們窩在沙發(fā)上,時而撒嬌著讓她再講講那些老故事,時而一起為一頓家常飯菜忙碌。我系上圍裙,笨拙地模仿她翻炒的手勢,看她在一旁笑著指點,廚房蒸騰的熱氣里,滿是幸福的味道。這哪里只是我的生辰,分明是屬于我們母女的“重聚日”,是用生命之線編織的珍貴紀念。
兒時的記憶里,母親的身影總是忙碌的。清晨,當(dāng)?shù)谝豢|陽光還未穿透云層,她便已在廚房中穿梭,為我準備可口的早餐。那“滋滋”的煎蛋聲,“咕嘟咕嘟”的煮粥聲,構(gòu)成了我童年最溫暖的起床曲。傍晚,當(dāng)我背著書包從學(xué)校歸來,總能在昏黃的燈光下,看到母親倚在門邊,眼神中滿是期待與牽掛。她接過我沉甸甸的書包,牽著我的手,將我迎進家門,那一刻,所有在學(xué)校的疲憊與煩惱,都在母親溫暖的掌心消散無蹤。
出嫁那天,母親幫我整理頭紗時,指尖微微顫抖。我望著鏡中她泛紅的眼眶,突然想起小時候她為我扎辮子的模樣。原來時光早已在她的眼角刻下細紋。婚后每次回家,我仍會像兒時般撲進她懷里,絮絮叨叨說著生活瑣事。她一邊嗔怪我“都當(dāng)人家媳婦了還不穩(wěn)重”,一邊把我最愛吃的零食塞進包里。后來我也成為了母親,深夜抱著啼哭的孩子喂奶時,忽然懂得了當(dāng)年母親獨自將我?guī)У饺耸赖钠D辛。那些無數(shù)個輾轉(zhuǎn)難眠的夜晚,那些為我操勞的日日夜夜,都凝聚成了最深厚的母愛。
如今,我已長大成人,離開了家鄉(xiāng),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多少個夜晚,透過窗簾仰望那一輪明月,思念便如潮水般涌來。我想起了母親的笑容,想起了她的嘮叨,想起了她為我做的每一頓飯,想起了我們一起度過的點點滴滴。我明白,無論我走得多遠,母親永遠是我最堅實的后盾,是我心靈的歸宿。
有人說:“母親是一本厚重的書,越讀越明白,越讀越覺得自己讀得太少。”是啊,母親對我的愛,又豈是我能輕易讀懂的?那是歲月里最綿長的牽掛,是時光中最溫暖的守候。我與母親的緣分,或許真的是上一世就已注定,這一世,我們相互陪伴,相互溫暖,走過人生的每一個階段。
月光依舊,灑在窗前,仿佛是母親溫柔的目光。
我知道,無論何時何地,母親的愛都將如這月光一般,永遠陪伴著我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而我,也愿用一生的時光,去珍惜這份難得的緣分,去回報母親那如月光般無私而永恒的愛。在時光的長河里,我們的故事仍在繼續(xù),就像那亙古不變的月光,溫柔地訴說著母女間最動人的情緣。

(編輯:吳存德;校對:霍曉霞;一讀:張飛、黃韻;一審:張燕青;二審:賈星慧;三審:王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