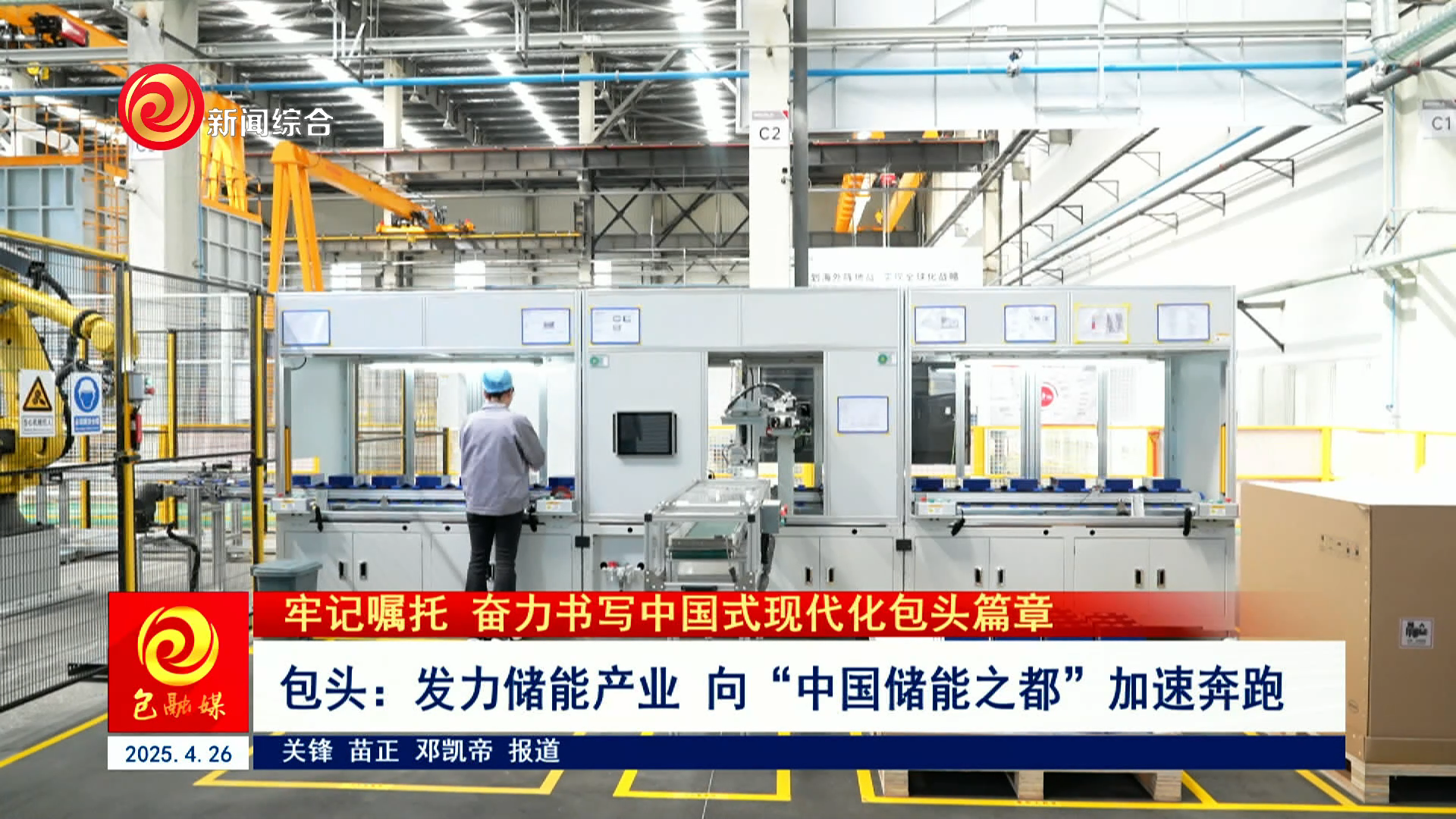《包頭日報》2025年4月23日 6版
午后的我市某書城,一排排書架前零星站著幾位讀者,而看電子書的座位上卻人頭攢動;在包頭市新華書店閱覽區(qū),一位青年人戴著耳機,手指在手機屏幕上滑動,屏幕上顯示著“帆書”APP的界面。這樣的場景,折射出數(shù)字化時代閱讀方式的深刻變革。
傳統(tǒng)紙質(zhì)書與數(shù)字聽書,孰優(yōu)孰劣?不同年齡群體如何選擇?近日,記者走訪我市多個社區(qū)、學(xué)校和圖書館,采訪了不同年齡段市民及教育專家,探尋在數(shù)字化浪潮的沖擊下,閱讀方式經(jīng)歷的深刻變革。
走訪發(fā)現(xiàn),隨著“聽書”模式在喜馬拉雅、帆書等平臺興起,“用耳朵閱讀”正成為市民的新選擇,傳統(tǒng)紙質(zhì)閱讀與新興的聽書模式并行發(fā)展,形成了“眼讀”與“耳讀”的雙軌并行格局。


共讀一本書
記者在昆區(qū)閱立方書店的閱讀角看到,市民劉強正捧著一本《額爾古納河右岸》細(xì)細(xì)品讀。他表示:“紙質(zhì)書能讓我沉浸其中,翻頁的觸感、油墨的香氣,都是一種享受。”像劉強這樣的傳統(tǒng)閱讀支持者不在少數(shù),他們認(rèn)為紙質(zhì)閱讀更有利于深度思考,尤其是歷史、哲學(xué)類書籍,更適合逐字逐句研讀。
然而,也有不少上班族表示更青睞于聽書。在包頭中科泰磁涂層科技有限責(zé)任公司工作的耿女士每天通勤時都會打開“帆書”APP聽書,“開車時沒法看書,但聽書能利用碎片時間學(xué)習(xí)。”
對于兒童而言,聽書的吸引力更大。包頭市昆都侖區(qū)第一實驗小學(xué)學(xué)生左弘翊說:“我最近每天睡前聽20分鐘《八十天環(huán)游地球》,因為主播的聲音很有趣,比看書更容易理解。”記者在走訪時發(fā)現(xiàn),許多孩子表示聽書可以同時做其他事情,比如畫畫、拼積木等,降低了閱讀的門檻。
但部分老師對此持謹(jǐn)慎態(tài)度。劉女士是一名小學(xué)教師,她認(rèn)為:“低齡兒童需要培養(yǎng)專注力,聽書容易分散注意力,而紙質(zhì)書能讓他們學(xué)會逐字閱讀,提升語文能力。”市教育局的“閱讀能力提升工程”也強調(diào),中小學(xué)階段應(yīng)注重傳統(tǒng)閱讀習(xí)慣的培養(yǎng),各學(xué)校通過設(shè)立“班級圖書角”“小荷書吧”等方式,鼓勵孩子們接觸實體書。
記者發(fā)現(xiàn),盡管不少青少年更偏向于聽書,但是我市各個學(xué)校都擁有濃厚的書香氛圍。走進(jìn)內(nèi)蒙古科技大學(xué)實驗小學(xué)的“小荷書吧”,琳瑯滿目的書籍令人應(yīng)接不暇,學(xué)生可以在這里舉辦讀書分享會;包頭市昆都侖區(qū)第一實驗小學(xué)每個班級里,都放置了書架和滿滿的圖書,不少學(xué)生正坐在讀書凳上沉浸閱讀……
“我們專門拿出一節(jié)課后服務(wù)課,全校統(tǒng)一進(jìn)行整本書閱讀。”內(nèi)蒙古科技大學(xué)實驗小學(xué)副校長郭詩韜說,學(xué)校設(shè)置“文溪風(fēng)荷”閱讀課程,以小荷閱讀課為主體,以書香研學(xué)和主題項目式學(xué)習(xí)為兩翼,激發(fā)青少年對閱讀的興趣。

學(xué)生沉浸式閱讀
在達(dá)拉特發(fā)電廠上班的“95后”職工劉俊偉,是“聽書”的忠實用戶。“每天開車往返兩地,路上需要將近兩小時。一邊開車一邊聽書,平均一天能聽完一本書,一年累計能‘讀完’200多本書。”劉俊偉向記者展示了手機里的聽書記錄,從《人間值得》到《微觀經(jīng)濟學(xué)》,覆蓋文學(xué)、社科等多個領(lǐng)域。
然而,包頭職業(yè)技術(shù)學(xué)院教師韓酈卻持有不同觀點。“聽書就如同吃速食一般,雖然看似省時,卻缺少了應(yīng)有的養(yǎng)分。真正意義上的閱讀,應(yīng)當(dāng)是親手觸摸紙張,在字里行間勾畫出重點,這種沉浸式的體驗是聽書所無法取代的。我平日里經(jīng)常參加線下的讀書會,與眾多書友一同潛心閱讀,并相互交流讀書心得,這種感覺特別棒。”韓酈說。
心理學(xué)教師楊勇強分析:“成年人選擇聽書的核心驅(qū)動力是時間成本。但認(rèn)知科學(xué)表明,聽書對復(fù)雜信息的處理效率低于視覺閱讀。例如,哲學(xué)著作的抽象概念需要反復(fù)回看,而聽書難以實現(xiàn)這一點。”

聽書愛好者選擇聽書書目
在包頭,市民們用行動展現(xiàn)出對兩種閱讀方式的靈活選擇。退休教師孫建國清晨打太極時聽《資治通鑒》,下午則研讀紙質(zhì)版;初中生羅宇用APP預(yù)習(xí)物理知識點,課后對照教材整理筆記。多名教育學(xué)家表示,閱讀的本質(zhì)是思想對話,載體變遷只是技術(shù)的外衣,能讓靈魂覺醒的就是好方式。
左弘翊媽媽表示,聽書時孩子容易走神,尤其是抽象概念較多的學(xué)科內(nèi)容,紙質(zhì)閱讀更能促進(jìn)深度思考,而且聽書平臺的算法推薦可能導(dǎo)致“信息繭房”,阻礙系統(tǒng)性知識構(gòu)建。所以她更鼓勵“整本書閱讀”,希望通過導(dǎo)讀課、讀書分享會等形式培養(yǎng)孩子們對紙質(zhì)書的喜愛,同時將聽書作為睡前故事或科普類內(nèi)容的補充。
《周宇和你讀經(jīng)典》欄目主持人周宇也建議,成年人可結(jié)合自身需求選擇閱讀方式,聽書更適合敘事性內(nèi)容,需要深度思考的書籍仍應(yīng)以紙質(zhì)或電子文本為主,同時應(yīng)定期進(jìn)行“主動閱讀”,如做讀書筆記、參與讀書會,避免知識碎片化。
在包頭的校園、圖書館、家庭乃至草原牧區(qū),閱讀方式的變革正悄然發(fā)生。正如新華書店包頭書城經(jīng)理張嵐所說,目標(biāo)不是非此即彼,而是讓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閱讀方式,讓書香飄滿鹿城。在這場“耳朵與眼睛”的閱讀之爭中,包頭市民用行動給出答案:夕陽下,賽汗塔拉城中草原旁,戴著老花鏡翻書的老人與戴著無線耳機的少年,共同構(gòu)成了傳統(tǒng)與未來和諧共生的美好畫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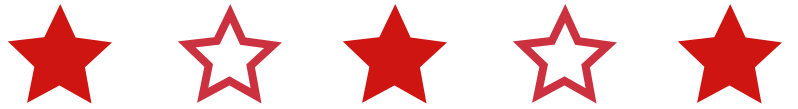
(策劃:張建芳 周旭;文/圖 記者:曹瑾)
(編輯:吳存德;校對:霍曉霞;一讀:張飛、黃韻;一審:張燕青;二審:賈星慧;三審:王睿)

聲明:包頭市融媒體中心原創(chuàng)作品。轉(zhuǎn)載請聯(lián)系授權(quán),注明來源于《包頭日報》微信公眾號(BaotouDaily)。
如果可以,請點點底部給小編加個雞腿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