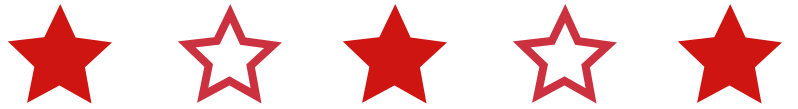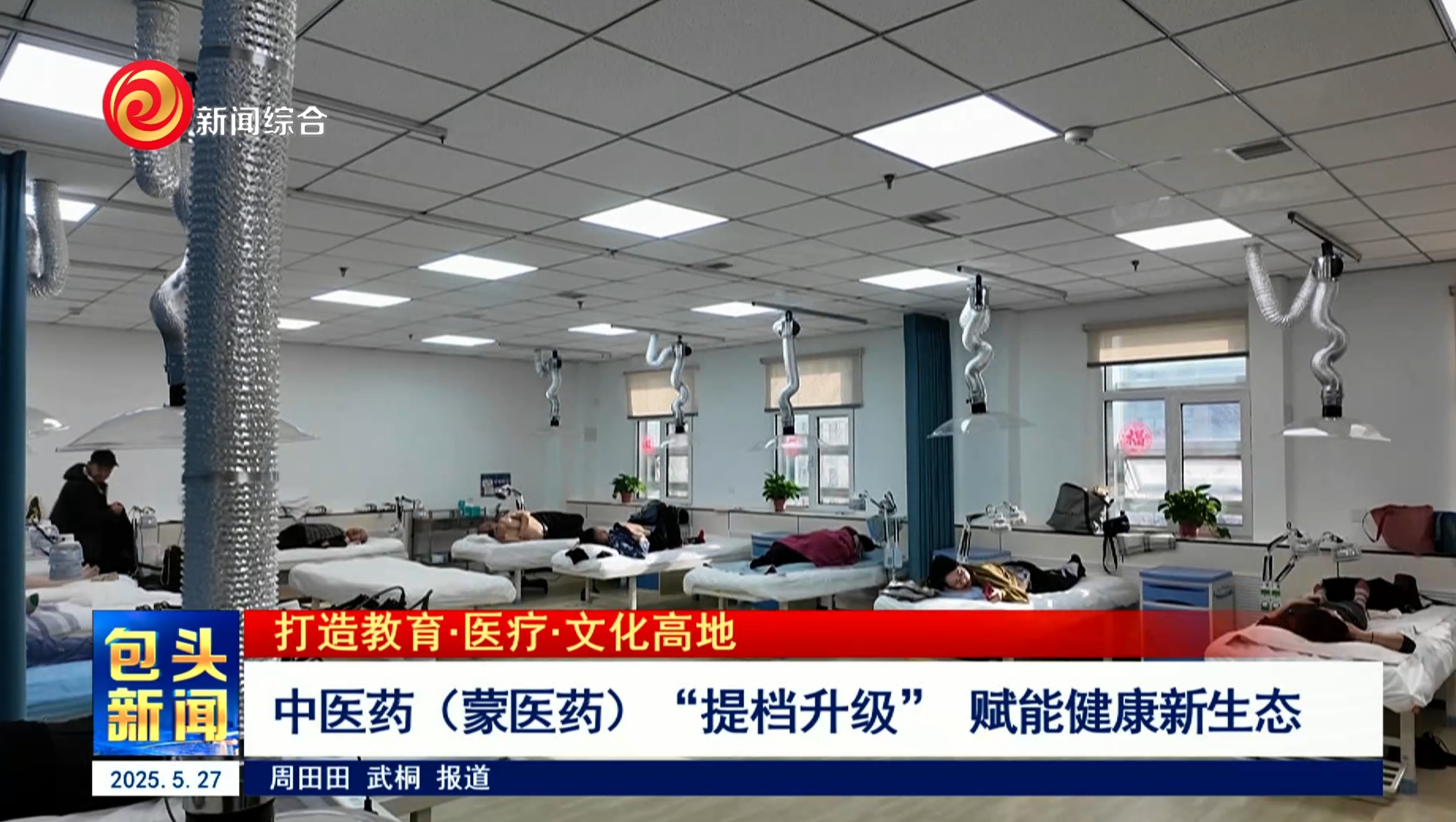5月的高郵市卸甲鎮(zhèn)周邶墩村,有了不一樣的聲音。
從村口下車,66歲的趙俊華緊緊地握著兩個弟弟的手,顫抖的指尖傳遞著跨越千里的思念。這一刻,時光仿佛倒流,將眾人帶回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。

時光回溯到上世紀(jì)60年代,經(jīng)濟困難和糧食短缺席卷江南,年幼的“巧云”隨著北上的列車來到包頭,她被送到包鋼醫(yī)院時,小臉通紅,哭聲微弱。
包鋼醫(yī)院退休醫(yī)生張甫生清晰記得當(dāng)時的情景:“對于這件事至今記憶猶新。這些孩子們年齡都特別小,身體也不太好,我們?nèi)横t(yī)務(wù)人員非常認(rèn)真,各個科室積極配合,經(jīng)過大家精心地護理和治療,孩子們很快康復(fù)出院。當(dāng)時我們醫(yī)院還發(fā)起捐款,大家都排著長隊為這些孩子們捐款,用于購買衣服、鞋帽等。”
作為包鋼第一代建設(shè)者的趙景山、沈秀蘭夫婦在醫(yī)院里見到這個皮膚白皙的孩子,沈秀蘭瞬間紅了眼眶。“多好的娃。”她將孩子摟進懷里,把溫?zé)岬哪唐窟f到孩子嘴邊。就這樣,來自江南水鄉(xiāng)的“巧云”,在包鋼建設(shè)的號角聲與草原人民的大愛中,在內(nèi)蒙古扎下了根,有了新名字——“小華”。
在趙俊華的童年記憶里,包鋼廠區(qū)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又充滿力量。養(yǎng)父趙景山總是在結(jié)束一天的忙碌后,把她抱在膝頭,給她講述包鋼建設(shè)的故事,耳濡目染下,“干一行愛一行”的信念深深地扎下。
北方的風(fēng)再烈,養(yǎng)父母給了她溫暖的港灣;冬夜再冷,一家人圍坐在爐火旁,聽著父親講包鋼建設(shè)的故事,便是最幸福的時光。10歲那年,弟弟趙振武的到來,讓這個家更加熱鬧。“養(yǎng)父母有一口好吃的也都緊著我和弟弟,我們的童年總是無憂無慮。”趙俊華說。
愛的回響伴隨著幸福的日子,趙俊華在呵護中長大、上學(xué)、結(jié)婚。女兒于靜的出生,讓沈秀蘭把更深的愛延續(xù)到了下一代。清晨的陽光里,沈秀蘭的自行車橫梁上坐著咯咯笑著的于靜,風(fēng)里都是甜甜的幸福味道。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,成了趙俊華記憶里最珍貴的寶藏。
在父親的影響下,趙俊華也成為一名包鋼職工。初入廠區(qū),轟鳴的機器聲與四濺的鋼花沒有嚇退她,她在弧光閃爍間開啟職業(yè)生涯。后來,為了照顧年幼的孩子,趙俊華從零開始學(xué)習(xí)縫紉技術(shù)。從穿針引線到裁剪縫制,她白天在車間里向老師傅請教針法,晚上在家中挑燈練習(xí)。憑借著包鋼人骨子里的韌勁兒,她很快掌握了勞保品制作的技巧。
在包鋼的歲月里,趙俊華與弟弟趙振武始終記得養(yǎng)父的囑托,無論是高溫炙烤的焊接車間,還是飛針走線的縫紉工坊,他們都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其中。
然而,歲月無情。當(dāng)養(yǎng)父母相繼病倒,趙俊華日夜守在病床前,一聲聲呼喚,卻再也無法留住他們離去的腳步。送走父母后的十幾年里,每當(dāng)看到熟悉的場景,聞到記憶中的味道,她的心依然會被刺痛。家里的老照片、母親織的毛衣、父親用過的茶杯,都成了思念的寄托。
2024年10月,一位朋友告訴趙俊華,包頭新建了“三千孤兒入內(nèi)蒙”主題展館,里面詳盡地展示了那段特殊歲月的點點滴滴。懷著復(fù)雜的心情,趙俊華踏入了展館。一進去,塵封的歷史照片、泛黃的信件以及充滿年代感的生活用品便撞入眼簾,瞬間勾起了她對故鄉(xiāng)的無盡思念。展館內(nèi),老人們講述當(dāng)年故事的影像在循環(huán)播放,他們的每一句話,都像一把鑰匙,打開了趙俊華記憶的閘門,讓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坐在火車上被送往內(nèi)蒙古的過往。“站在展館里,我的心跳都加快了,那些沉睡多年的記憶瞬間被喚醒,尋找親人的渴望前所未有地強烈。”趙俊華說。
這次參觀成為了趙俊華尋親路上的關(guān)鍵轉(zhuǎn)折點。渴望尋親的念頭一旦埋下,便在她心里生根發(fā)芽,讓她念念不忘。不久后,同是“國家的孩子”的李焱飆打來電話,兩人在交流中,相似的感受、共同的心愿,將他們緊緊牽絆在一起。在李焱飆的鼓勵下,趙俊華下定決心,參加了DNA檢測。等待結(jié)果的過程是煎熬的,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無限拉長,趙俊華在糾結(jié)與期待中苦苦等待,無數(shù)次設(shè)想結(jié)果出來后的場景。
終于,好消息傳來。當(dāng)志愿者發(fā)來比對結(jié)果時,趙俊華顫抖的手幾乎握不住電話,親情的呼喚有了回響,故鄉(xiāng)找到了。然而,親生父母早已離世。

再回首這段故事,大弟弟王其金和二弟弟王其海都忍不住流淚。“姐姐離開我們這個家,成為父母永遠(yuǎn)的痛。記憶中這個未曾謀面的姐姐是父母最大的遺憾,直到老人臨終前依舊放不下這件事,囑咐我們一定要繼續(xù)尋找。”王其金回憶著過去幾十年的記憶,姐姐“巧云”是一家人的牽絆,是父母的遺憾,而尋找姐姐是他們兄弟一生的使命。“我們想了很多辦法,也托了很多人,打聽了很多渠道,但是關(guān)于姐姐的去向只停留在從上海丟失后被一家人收養(yǎng),后來那家人的消息就斷了。”幼年的意外,帶來了六十多年的傷痛。“我想讓姐姐回家,我想今生見一面我的親姐姐,有這個念頭我就不能放棄。”弟弟王其金把尋親作為一種執(zhí)念。
2024年7月,王其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做了一個DNA檢測。他說:“原本以為這一次同樣消息渺茫,誰承想,今年4月21日,戶籍所在地卸甲鎮(zhèn)周邶墩村相關(guān)工作人員打來電話,姐姐有消息了。曾經(jīng)幻想過多少次姐姐的樣子,甚至是否還在世。”諸多的不確定性沒有打消這對兄弟尋親的念頭。
“得知找到姐姐的消息,我?guī)缀跆焯烊ツ沟乜蓿嫖繋еz憾離開的父母,他們掛念了一生的女兒要回來了。”王其金和弟弟把老房子掃了又掃,規(guī)劃著和姐姐一家未來的生活,這個遲到了六十多年的團圓時刻真的來了。
5月22日,高郵市認(rèn)親儀式現(xiàn)場,包鋼集團作為“娘家人”也派代表到現(xiàn)場,見證這場團圓時刻。“我很驕傲,我很自豪,都是我的娘家人。”趙俊華激動地說。

這場遲到的團圓,不僅是一個家庭的圓滿,更是“齊心協(xié)力建包鋼”與“三千孤兒入內(nèi)蒙”兩段佳話的完美交織。它見證了全國人民支援邊疆建設(shè)的磅礴力量,也訴說著草原母親跨越血緣的無私情懷。當(dāng)包鋼“娘家人”與高郵鄉(xiāng)親并肩而立,我們看到的是中華民族守望相助、血脈相連的精神傳承。這份跨越時空的愛,終將化作永不褪色的時代記憶,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。